
英國獨立記者哈莉特‧威廉森(Harriet Williamson)最近發現一個問題:媒體業越不景氣,藍領家庭出身的子女就越不可能進入這個產業。不是因為他們發現此行前景黯淡不願挑戰,而是自己的經濟條件需要立刻就業,導致根本撐不過無薪實習的階段。這使得媒體的觀點越來越單一,因為只有在私立學校受教育、出身富裕權貴的特定階層(白領與白人)才能進入媒體業。最終,精英階層不僅主導著政經界,更掌控了整個國家的輿論走向。
她發現,很多同行的父母是已經在媒體界待很久的大老,不然就是靠父母的人脈關係「被推薦」進來,很少看到跟自己差不多背景的同齡人,她寫道:「因為藍領階層必須先撐過無薪實習的階段,必須有其他經濟來源支撐倫敦高昂的生活費用(富家子女則有父母供應)。在美國,紐約媒體業的實習現況也是如此。」
若沒有富爸爸富媽媽的支援,想熬過無薪實習的階段難上加難,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卻是進到媒體業的唯一途徑。如今,英國媒體業幾乎完全以倫敦的精英階層為核心,透過裙帶關係、人際關係,以及艱難的無薪實習制度(經常持續數個月或更久)等方式用人。當然,目前還是有專門招募應屆畢業生的方案,但競爭總是非常激烈,而且很多時候只能從地方媒體做起,再慢慢爬到全國性媒體。然而,當這些畢業生還在地方媒體起步時,其他靠關係進去的人早已在全國性媒體做事。隨著落差越來越大,最後主要還是以精英階層來主導媒體。
很明顯,英國媒體的人才現在幾乎都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主(美國則是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其他學校根本沾不上邊。即使是駐外記者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名年輕剛畢業的記者,想要從事低薪且風險高的駐外記者工作,肯定需要家裡的經濟支持。於是,這造就了更多來自富裕和特權階層的駐外記者,相較於藍領出身的記者,他們可能對於更尖銳敏感的問題視而不見。

無論是國內還是駐外記者,藍領出身的記者長期處於弱勢,而且經常不受重視。為了完成無薪實習的階段,你每個月都得煩惱還有多少錢能撐下去,而那些特權階層的同事早就拿到正式員工的職位。就算真的熬過來得到的也是一份不安定的工作,不管你再怎麼努力,只要一次失誤就可能讓你失業回到默默無聞的過去,因為你沒有經濟條件可以重來,或是靠關係跳到另一間公司。
但白人精英階層出身就不會這樣,特權與人脈在這個產業總是很管用,有關係就沒關係。以英國首相強森為例,他早年也是在新聞媒體業工作,但1988年因為「杜撰引文」遭到倫敦《泰晤士報》解雇。然而,他很快地就被《每日電訊報》錄取,原因很可能是他在牛津大學擔任學生會會長時與該報主編麥克斯‧赫斯廷斯(Max Hastings)熟識。
解決多樣性危機的重任落在精英階層掌控的媒體肩上,他們可以拒絕因父母身份而憑空出現的工作機會和安排來改變現狀。哈莉特‧威廉森認為,英國媒體業應該積極從其他地方聘用藍領出身的記者,而不是一味地使用牛津、劍橋或其他傳統私立大學的畢業生。無薪實習的制度也必須改變,因為它把沒有經濟條件的人排除在外,才能與想法也應該永遠優先於關係。
如果失去了多樣性的觀點,媒體業就會淪為自爽的小圈圈。裡面只存在相同的敘事、概念和觀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如果沒有不同背景的人的聲音,媒體就很難與現實社會產生共鳴或連結。

看完英國的情況,我們或許好奇這個問題在台灣會發生嗎?貧富差異可能沒有,但自國民政府統治以來,媒體業一再美化國民黨政權與宣揚大中國主義的觀點和思想,例如把最大的新聞系所設立在黨校「政治大學」,原本的用意是訓練政治作戰傳播,而非把新資訊和自由觀點帶給社會大眾。即使解嚴之後情況也沒有轉好,大多數從業人員乃至媒體高層還是繼續外省特權階層的自我複製,其人數不成比例的高,導致本省籍沒有話語權。在政權輪替之後,這群人失去了過往阿諛奉承政府的目標,雖然媒體看似擁有了新聞自由,卻沒有培養出相應的專業水準,轉而變成現在異常可怕又墮落的樣貌。
2020年卓越新聞獎的得主在獲獎時也批評,台灣媒體業不被尊重是因為毫無專業倫理可言。沒有倫理的最根本原因,她認為是因為這個產業本身是極權時代殘留下來的闌尾,而記者的專業傳統並非一夕之間就能養成。
威廉森的總結則寫道:「健康的媒體是民主正常運作的象徵,我們必須讓它存在,而我們也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多樣性的觀點。」
參考來源:Foreign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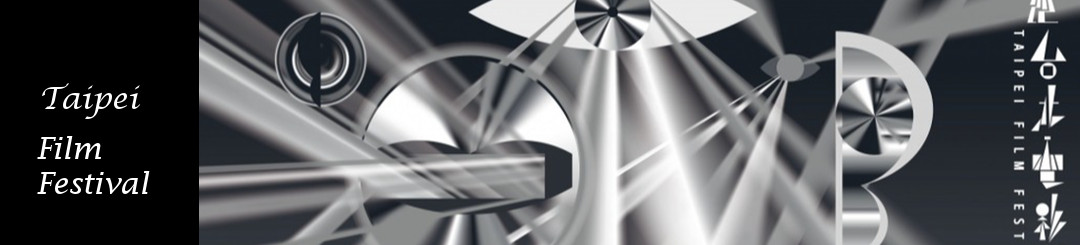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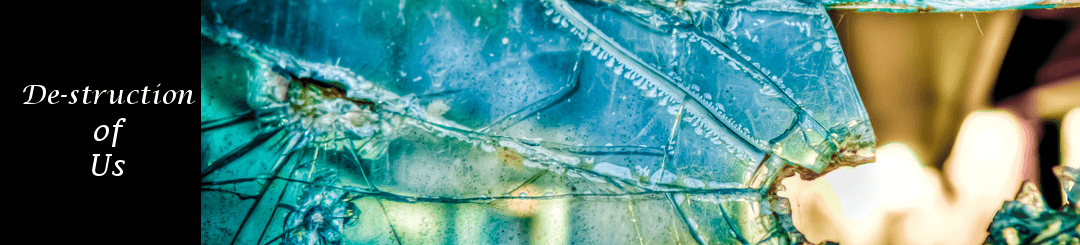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