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新自由主義與虛假的烏托邦:Daniel Zamora訪談
2016/06/05 10:00
譯按:比利時的青年學者Daniel Zamora於2014編輯的《批判傅柯:8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的誘惑》一書中,指陳了傅柯晚年與新自由主義思想之間的曖昧關係,而左派日後在社會治理論述的孱弱,部分來自於無法擺脫傅柯的思想幽靈,該書英譯本於2015年12月以「傅柯與新自由主義」之名出版。該訪談由喬治梅森大學的文化研究學程座談會進行。

採訪|Dave Zeglen 受訪|Daniel Zamora
摘譯|睫狀肌
讓我們從你引發爭議與論辯的主要論點開始:傅柯是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在那個政治風向紊亂的70年代,他實際上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而在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問題上,他的思考又是如何變動的?又是什麼樣因素與脈絡,促成了傅柯對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公開反對呢?
這些都是需要追問的重要問題。不把傅柯的作品放回70年代法國本地脈絡,我們是無法理解傅柯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更無法了解日後「老」左派與「新」左派的衝突,以及後68左派與戰後左派之間逐漸高張的對立。
並不是很難看出傅柯對戰後左派方案的反感,他很明顯敵視馬克思主義。在題為〈如何擺脫馬克思主義〉(How to get rid of Marxism)的日本期刊訪談中,他說「在根本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不外乎就是「一種權力的樣態」,他這麼闡述,「實情是馬克思促成了政治想像的貧乏,現在也依然如此,這是我們的起點」。在與「新哲學家」Bernard Henri-Levy的訪談中,傅柯討論了革命的問題,對1977年的傅柯來說,「重回革命,正是問題所在…你很清楚:革命的欲望本身正是問題所在」。
這個主張非常有意思,傅柯不只是駁斥了革命的理念,在左派聯盟可望在1978年的議會選舉拿下勝利的脈絡之下,他還影射了「重回革命」。不要忘記,在1972年到1978年那段時間,三個團結在左派聯盟的政黨:法國共產黨、社會黨與左派激進黨(MRG),於1972年在「共同方案」(common program)達成共識,要求銀行體系的國有化、減少工作天數、擴張社會安全機制以及提供工資等等。支持者把「共同方案」看作是在法國階級關係中,引入結構性的經濟轉變,終極目標是「往社會主義的大路」。
因此,傅柯在英語世界的引介者Colin Gordon說傅柯顯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支持任何對現有體制做出革命性變革的社會主義時,他是對的。但他與其他許多人不會承認(或者有意忽略)的是,傅柯不只是反對馬克思主義,他也反對由其衍生出來,更為廣泛的「政治想像」。傅柯不僅僅反對作為政治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總的來說,他也反對作為戰後左派擘畫政治圖騰的馬克思主義:這個擘畫包含了強健的工會,以及激進的社會主義組織。
也就是說,那時傅柯與許多知識分子群起對抗的,不只是某種外來社會主義(例如,蘇聯版本),還是法國本地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他在1977年說「所有社會主義傳統在歷史創造的一切都要譴責」的意思,而這也是他在1981年不投密特朗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這件事情的份量,你得理解,那場選舉並不是一場爛蘋果之間選一個比較不爛的選舉,恰恰相反:密特朗得到了70%勞動階級的熱切支持,他們把這場選舉視為社會改革的契機。因此傅柯不投密特朗,不只是超乎尋常,而且還令人訝異。
雖然,我們後來知道,期待中的改革並沒有發生。但傅柯在1981年不投密特朗不只是關乎一次投票,它所披露的是,傅柯對於左派在1945年後整體政治擘畫深表懷疑,包括強有力的國家、普遍的權利以及公共服務。「新哲學家」Andre Glucksman在《大師級思想家》中──一本傅柯寫了長長書評大為讚賞,並稱之為「相當傑出」的書──總結了傅柯的思緒,「我們贏來的,只是用公務員代換資本家嗎?」,在傅柯看來,「長期來說,國有化就是宰制」。
因此,在這個反覆駁斥「老派」社會主義的脈絡中,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似乎讓傅柯與許多後68的知識分子很感興趣。新自由主義給了他們一個思考「反國家」的左派會是什麼樣子的契機。附帶一提,這也讓我們知道應該要如何理解傅柯的《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傅柯把部分興趣放在法國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與Raymond Barre的新自由主義政治,以及德國Helmudt Schmit的社會民主黨。對70年代晚期新自由主義治理性崛起有興趣的人來說,傅柯這個選擇確實有點奇特,為何不提皮諾契特的殘酷軍事政變?以及接下來在智利展開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呢?傅柯為何只關注非常理論性的新自由主義,而完全不考慮當時正在智利上演,接著雷根與柴契爾馬上就要登場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及其保守後果?他甚至完全不討論海耶克對民主的菁英式理解,或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對智利軍事政變的辯護。
於傅柯晚期作品這個耐人尋味的偏愛,Serge Audier闡述了一個理由,他認為如果讓傅柯感興趣的是彼時的新自由主義,部分原因是德法兩國新自由主義治理的良好關係,以及這個關係對於社會主義未來的意義。如他所說,「如果傅柯採取了一個德國中心的觀點,這是因為他對法國與法國社會主義在1979年的命運感到懷疑,假如法國的政治看起來像是師法了德國的社會民主政策,那麼社會主義在今天意味著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傅柯的生命政治講座看起來非常關心左派聯盟在輸掉1978年選舉之後面對的危機,以及整個戰後左派的政治擘劃。
不理解彼時法國的政治與智識脈絡,就很難掌握傅柯最後十幾年書寫的全盤意義,或說,至少他對新自由主義與政治的反思。不要忘了,彼時傅柯認為法國左派沒有適切的「治理性」,換句話說,社會主義者還沒能開展出自身的治理理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對於重新思考左派──重新思考怎麼把革命跟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擱到一邊──其實非常吸引人。
你說從傅柯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興趣中崛起的惡果是勞動階級的核心地位被「新大眾」(new plebians)取代,助長了今天左派的「流氓觀念論」(奈格里、哈維、紀傑克與馬庫塞等人),對你來說,這個代換付出了什麼代價?
在68之後,這個轉向關注「邊緣」薪資勞動者的勢頭十分強勢,眾所週知,馬克思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的東西,對於法國毛派團體,特別是「無產階級左翼」(La Gauche Prolétarienne)的奮鬥來說非常重要。這個團體在1968年到1973年之間對知識圈具有不容小覷的文化衝擊,他們積極組織行動為移民、無照勞工與囚犯發聲。法國毛派之一,傅柯的伴侶Daniel Defert這麼說,「新的認同化原則正在取代勞動階級文化在19世紀創造出來的一致性」,也就是說,邊緣或被賤斥的團體具有相對於「無產階級鬥爭場域」的「自主性」。
傅柯在1972年,把這些新的鬥爭稱為「一個關乎新大眾出現的全新現象」,這構成了勞動階級中的「非無產化」游擊隊。當傅柯的分析轉向對治理性與生命權力的研究時,這些被他說是「行為舉止上的反叛」的鬥爭,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對傅柯而言,問題已經不再是「剝削」與「不平等」,更關乎「微觀的權力」以及「宰制體系的播散」,更關乎「更少地被治理」,而非「奪取」權力。如傅柯自己所說,問題「本質上是權力自身,這遠遠超乎像是經濟剝削與看起來像是不平等的那些東西,而這些鬥爭的核心關注在於這個既有的權力是被強加的,而這是無法忍受的。」
從這個轉向中很明顯的是兩種左派政治根本不同的形式,一個的目的是消除差異與階級結構,而並不單只關注權力的運作方式,問題無關乎剝削的「殘酷」或其「常態化」效應,而是關乎存在著剝削與不平等這個事實。
而傅柯的思路代表了另一種版本,他的分析關注散佈不平等效應的過程,而非始作俑者。勞動市場的各種歧視、汙名與賤斥形式,所創造的既非失業,也非不穩定就業,而是顯然構成了階級中,不同於無產階級的新生力軍。
我要強調的是,並不是說許多過去被忽略的宰制形式已經得到重視了,而是傅柯等人的理論工作漸漸地跟任何剝削的概念說再見這個事情,傅柯並沒有提出一種檢視賤斥與剝削關係的理論視角,反而逐漸把兩者對立起來,甚至是相互扞格的原則。
政治行動的核心,從勞動階級轉向到更「邊緣」的團體,沙特說,這究其本質是一種「道德姿態」,以及某種「道德馬克思主義」的崛起。它的道德面向在於它的關心是「少數」、「邊緣」與「被賤斥」,以及宰制與歧視的議題。在這些政治行動中,歷史學家Julian Bourg很精確地看到法國左派的倫理轉向,這個轉向不僅僅只是改變了如何改變社會的主題,也「革了革命這個概念本身的命」。長期來看,這個變化導致「人權」代換了「階級鬥爭」,在很多面向上,這與資本主義完美地相容。在這點,稍微提一下傅柯在1981年〈反治理,人權〉(Against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這篇文章其實很有意思,傅柯在該文中高度讚賞了像是國際特赦組織這種NGO,並在這些人權組織中,看到了抵抗治理性的新政治形式,以及政治行動的另類選擇。
所以,回到你一開始的問題:傅柯對於國家與各種壓迫機制所打造的常態化形式的關注,同時也是他對新自由主義興致昂然的原因。他認為新自由主義代表了一種新治理性的有趣形式,一種對人的行為舉止不甚關心的形式,這麼看來,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性可能會比較不那麼「規範」。
但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傅柯並沒有把新自由主義看成創造「大眾消費」同質化社會的嘗試(這是德波或馬庫塞的想法),他是把新自由主義理解成一種創造差異的治理性。在他的講座,他幾乎都快要給德國的新自由主義打上一層烏托邦的蠟,傅柯主張,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思想「相反,它要的不是一個以商品,以商品的整齊畫一為目標的社會,而是以企業的紛雜與差異為目標的社會」。
第二,後68左派對於德斯坦在1974年的掌權,以及他帶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抱持不小期待。他對於青少年、囚犯、女性與移民等問題的改革,更被傅柯視為法國「新的治理性技藝」的發展標記,而這能讓左派從國家中抽身出來。
在您編輯的這本書中,社會學家Loic Wacquant指出美國的大規模監禁問題,對於左派來說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美國的監獄所關押的,包含了勞動階級中,被「去無產」的組成,不把他們關起來的話,這些人不管是政治上與治安上,都讓人棘手。跟其他國家相比,不管是人口平均還是原始數字,美國確實都關押了為數更多的人,對左派來說,這難道不會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助力嗎?
這個問題直指左派消沉的核心,從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來,工業化國家的失業節節攀升,美國的現象可以說是用刑事手段對付失業問題的結果,歐洲固然沒有大規模的監禁,但是,歐洲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所得不平等惡化,「失業不平等」也是,我用這個詞指的是最富有的人落入失業,與所得分配最底層的人相比的風險比率。與貝克(Ulrich Beck)與鮑曼(Zygmunt Bauman)所推廣的想法不一樣,至少就失業風險比率來說,看起來更像是財富不平等分配的進化,也就是說,從70年代開始,失業已經往勞動力的某個特定部分高度集中,根本沒有概括承受風險這種事。但很不巧,階級不平等不再至關重要這個誤入歧途的觀念,卻成了理解社會問題的基調:社會的問題越來越被看作是排除與賤斥的問題,而非剝削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左派以道德與倫理的詞彙來理解這些問題,把它們從資本主義的整體問題中分離,後果後患無窮,也有一套道德論述的右派,開始用類似反對「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不要領救濟金的「特權人生」以及別讓政府養等等鋪天蓋地的論述,贏得部分勞動階層的鼎力支持。
面對右派對勞動力量的分化,左派並沒有想出辦法克服,反而是把社會上的分化,轉化成政治議題(更確切地說,是倫理議題)。就像社會學家Michèle Lamont曾經指出的,這個轉化重新形構了勞動階級的象徵性疆界,突出了族群─種族疆界,並激化了它與勞動階級之間的對立。若是說這個惡鬥,必須為許多社會權利的倒退負上部分責任,那我們勢必也要承認,從「階級政治」撤守,轉向捍衛據說被排除在「薪資勞動」之外,勞動階級的邊緣碎屑,不會是好主意。
我們現下需要的,是一套能把勞動階級團結起來的策略與綱領,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的,我們得把「失業看作是剝削的範疇」,而不只是某種不穩定的「狀態」,或者可以從受薪階級的被剝削中切割出來的「情境」。對於「被賤斥排除」的討論,不能跟資本主義在結構上必然要創造失業後備軍的分析分開來看,資本主義要排除的是社會所有群體,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要賤斥的是全世界人類的所有群體。對我來說,這個觀點意味著有必要重新訴諸一個普遍性的綱領與權利,能夠處理市場的不平等效應問題,同時得要讓影響我們生活至為巨大的部門「去商品化」,而做法絕對不是讓市場運作得更順暢,更是要限制市場。
原採訪出處:EDGES BLOG: CSC Interview with Daniel Zamora(本文為節譯)
今天畫點什麼?《路茲先生的經典插畫技法書》
MPlus Book Preview
2016/06/04 10:05
人類為什麼就是愛吃肉
Mumu Dylan
2016/06/06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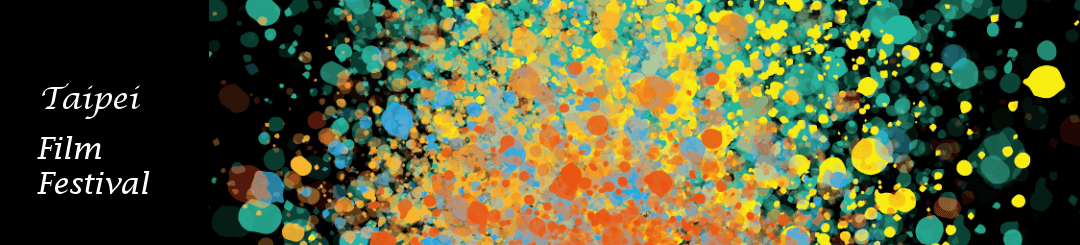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mplus
追蹤mplus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分享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