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芙妮‧莎爾菲生於一九二八年,長於倫敦及英倫三島。二十一歲生日剛過,她就贏得了當地雜誌的封面女郎競賽,加入了倫敦的蓋比.楊經紀公司,接受模特兒的訓練。她擔任過藝術家的模特兒,駐店模特兒,商業廣告模特兒,出現在各種的廣告中,從服裝到早餐穀片到杜松子酒。她的先生吉姆.史密斯投身於劇場以及電視製作,結婚之後,黛芙妮就放棄了模特兒生涯,搬到赫特福德郡,養大了三個孩子。今天她仍住在那裡。在先生過世之後,她突然又被發掘了──以七十歲的高齡。從此一直忙於工作。

文|黛芙妮‧莎爾菲(Daphne Selfe)
譯|趙丕慧
它不是玻璃鞋,而是一隻白色帆布鞋,只有一條繫帶,楦頭窄,路易跟,一九一五年夏季風靡了所有時髦年輕的女性。但這隻鞋在我家卻和灰姑娘掉落的玻璃鞋一樣重要──因為,少了它,我的父母可能壓根兒就不會相遇。
這隻鞋叫「吉布森」,是經典鞋款,以美國雜誌《哈潑週刊》中亮麗的吉布森女郎為名──真不知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行銷術!有天下午,在薩福佛克郡的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一家旅館,這隻鞋從陽台上掉了下去,落在下層樓的陽台上,被一個三十好幾的教書匠發現了,不過他那個人可能連瑪麗珍鞋和牛津鞋都分辨不出來。
法蘭西斯‧莎爾菲是一名文靜謙遜的人,到洛斯托夫特來享受著名的海灘、碼頭與日出。同行的還有他剛從印度回來的哥哥嫂子,以及他們六歲大的兒子約翰。洛斯托夫特在那個年代是度假的首選,從一七六○年代起就是旅遊勝地,那時首次引進了海水浴場的更衣車,而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這裡仍和東英格蘭的另一個熱門景點克羅默(Cromer)競爭激烈。
法蘭西斯從陽台上拾起了這隻鞋,然後上樓去,敲了在他房間上方的房間門。
「不知道這隻鞋是不是你們的?」他害羞地問。
誰的腳能穿下這隻精美的鞋子呢?樓上的這個房間住的是一大家子,蓋洛威家族,而就是這麼巧,最年輕的那個站出來認領鞋子。她是一位豔光四射的二十二歲女郎,名叫愛琳,親朋好友都暱稱她「寶貝」──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愛爾蘭美女,赤棕色頭髮,深邃的藍眸,高高的顴骨。就在幾分鐘前,她洗好了鞋子,放在陽台上曬乾,誰知有一隻鞋竟掉了下去。
「對,是我的,」她說,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真對不起,還麻煩你特地送上樓來。」
「沒事,」他喃喃說,盡量不要瞪著人家看。「不麻煩。」等我父親終於自我介紹時,他已經墜入愛河了,可是還沒到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時候。兩家人成了朋友,愉快地一起散步、曬太陽──而他就在某個時間點向我母親求婚了。可是她不願意。
幾十年後,我可以從他們回憶初識時的語氣聽出來他們一見面就有火花,可是追求媽咪的人早就有一長串了。她的仰慕者包括無線電之父馬可(GuglielmoMarconi),而且出名的肖像畫家傑拉德‧雷‧杭特(Gerard Leigh Hunt)也為她畫過肖像。她是公認的大美女,人見人愛,所以她有挑三揀四的自由──而且我父親對她來說有點老。畢竟是十五歲的差異。她不覺得嫁給年紀大的人是好主意。不過,他們仍在假期結束後保持聯絡。
爸爸因為視力太差,沒法赴前線作戰,只好當民防隊員,繼續教書。他在大戰期間定時寫信給我母親。那個年代大家很常寫信。我覺得她大概是懶得回──就算回了,也不是很頻繁。他們兩人或許曾偶然在沙龍或晚宴相會,我母親會在這類場合自彈自唱。她是位極有音樂天分的人。無論如何,如果爸爸知道接下來的幾年裡她忙著跟別人訂婚的話,他一定會很痛苦。
她的第一位未婚夫叫哈利‧賽特佛,後來她又和湯姆‧凱德訂婚。兩位男士都戰死沙場。我不知道對她的打擊有多大。部分是因為二十多年過去了,在我聽說這回事的時候另一場戰爭的烏雲又已罩頂。即使是在那時,我聽說的也不多──可卻阻止不了我繼續打聽。有時候是斷斷續續的。大家都不太願意談感情。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心碎了一次,或兩次,抑或是她掉進了在火車站月台上送別的漩渦,幾乎不認識她答應等他們從前線回來就嫁給他們的那些男人。訂婚在那段歲月裡是很寬鬆的一個詞。妳差不多要先跟某個人訂婚,然後才能跟他出去約會。社會規範不一樣──那是個整體而言大為不同的世界,那麼多的男人戰死,所有的英國年輕女性也不能再挑三揀四了。我的很多阿姨姑媽和她們的朋友都是單身,就是因為大多數可以嫁的男人都遠赴異地,而且只有少數人回來。

另外還有別的地方需要適應。在戰爭的年代裡,女性需要工作,媽咪在英國銀行得到了一個人人垂涎的職位,完全是因為她寫了一筆的好字。這可是百分之百的轉折,因為我外祖母在我媽咪畢業之後沒有准她去找工作。銀行非常注重安全,她被鎖在籠子裡幾個小時,忙著記帳本,但至少還有七道菜的晚餐可以期待。人人都在挨餓,銀行的人卻每天晚上都有盛筵。
女性的時尚也在成熟。巴黎發生了大事,那裡不管什麼都變得「摩登」。極具影響力的設計師保羅‧波烈(Paul Poiret)以簡單寬鬆的設計以及他對層次的熱愛,幾乎是隻手終結了維多利亞式緊身褡。波烈的絲質和服式外套紅極一時;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的無袖襯衣式洋裝鼓動了更自然的線條;珍‧浪凡(Jeanne Lanvin)設計的夏季直筒洋裝釋放了女性的身體,解開了之前那種漿過的布料的束縛;而且現代的胸罩也發明了(萬歲!)。僵硬的衣料以及鯨魚骨裙撐遜位,換上的是流動的絲緞棉毛料。下襬線拉高,露出了一半的小腿肚,腰線放鬆,泳裝則露出了膝蓋──不過大多數的女性仍在泳裝底下穿長襪,不管是在海裡還是在海灘上!
我母親當然愛上新的輪廓。她當年是個很時髦的女孩,而且終其一生都對時尚很敏銳。她總是穿著得體──也要我一樣──即使是在她的晚年。我也樂於幫女兒打扮,讓她開心,因為她喜歡孫女跟得上流行。「妳今天穿了什麼?珂蕾兒和蘿絲穿的是什麼?」她會這麼問。
所以她當然不會放過主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雜誌的那種較飽滿較短的裙子,也就是「戰時大蓬裙」,這種款式終於讓女人能夠行動自主,而不是到哪裡都只能邁小碎步。不過這種裙子也引起了爭議,很多人不是嫌它在物資短缺的年代耗費太多布料,就是怪它的裙長不成體統。可是時尚作家宣稱這種裙子有「愛國精神」,因為即將開拔的士兵看到女人的腳踝能士氣大振,這點我舉雙手贊成。
隔年的時尚變得沉穩,女性多穿著比較保守的服裝,以便配合全國的嚴肅氣氛。你不管往哪個方向看,都會看到有人在為兒子、為兄弟、為丈夫服喪。戰前柔和的粉彩,戰爭剛開打頭幾個樂觀的年月裡大家喜愛的大膽色彩如今幾乎看不見了,而且軍方的影響也悄悄滲透了最新的外套、鞋子以及大衣的設計,同樣的情況在二次大戰又重現了。
媽咪第三次訂婚,對方是柏特‧溫莎,他熬過了大戰,可是兩人的關係生變──不過仍保持聯絡,而且我記得在我結婚之後還見過他,非常喜歡他。這時,我父親仍然耐心地等待。他是找到了意中人,可是她也讓他受盡了相思之苦!
儘管他不是媽咪的第一人選,我卻覺得我母親其實真的很適合嫁給一個較年長的男人。她的父親在四十二歲時猝然過世,那時她才九歲,我覺得爹地填補了那個恐怖的空白。他是那種溺愛的、家長式的丈夫,而且他珍愛她。也許她一直都在尋找一個父親角色。

她必定很渴望安全,因為她的家庭在她父親過世後度過了朝不保夕的歲月。我的外祖母愛蜜莉‧蓋洛威真的是含辛茹苦拉拔大了五個孩子。沒有健保,沒有社福,拖著那麼多孩子,又沒有丈夫!真不知道她是怎麼熬過來的。她的哥哥福瑞德顯然幫了她大忙。我沒見過他,可是聽起來他就是個重手足之情的大好人。
我的外祖母愛蜜莉對混亂和激變一點也不陌生──對照她艱辛的一生,或許能說是幸運吧。她的家庭在一八五○年代的愛爾蘭大饑荒出走,前往紐約,而她在一八五九年出生。但十年之內,他們又移民了,這一次是到北倫敦的斯特拉格林區(Stroud Green)。她嫁給了我的外祖父,那年她二十一歲。不幸的是,粗心大意的保母從嬰兒車裡要把她的二女兒朵拉抱出來的時候,卻失手把她摔死了。但我不覺得那一輩的人會像現代人一樣把那種事當成是莫大的個人悲劇。他們缺少知識,也不談這類的事情。什麼心理分析根本聽都沒聽過,也沒有諮商,沒有外在的協助。你的朋友家人幫助你解決麻煩,而日子照樣得過下去。一切都看你的內在有多堅強──而愛蜜莉外婆是非常堅強的。
我母親在一八九三年出生,是家中第六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大家都叫她「寶貝」愛琳。她很有音樂天分,跟她母親一樣既堅強又積極,很早就學會了要在不如意時不失望氣餒。據我所知,人生唯一讓她失望的一次就是她去參加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入學試,僅以一分之差落選。害得她精神崩潰,起碼她自己是這麼說的,儘管我從來也沒看過我媽咪有絲毫脆弱的心理狀態。不過呢,一定沒有那麼糟,因為她繼續學音樂,每天花四小時彈鋼琴,而且在倫敦城的各處演奏,在共濟會晚宴和威格摩爾音樂廳之類著名場所的音樂會上表演。我還留著一些節目單,因為我有收集癖。
媽咪和她的姐姐歌緹跟著一位老師學歌唱,他叫斯邁,是偉大的義大利歌劇演唱家恩里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的朋友。媽咪說他的長相就像卡魯索,住在一條小後巷的頂樓,聽起來還滿浪漫的。他跟媽咪說她的嗓音像天鵝絨,而在他傳授了她所有歌唱的基礎之後,她開始在金斯頓(Kingston)的班托百貨公司茶舞會唱下午的四點場。里奧納‧班托是我們家的好朋友。大戰期間,她在聖馬田教堂、斯金納堂、魚販會堂演唱。
蓋洛威家是很愛交際的家族,每個月的第二個週二都會舉辦音樂會。客人都會帶著樂譜或是詩集來,人人都換上最好的衣服:短晚禮服,羽毛扇子,購自牛津街角的波何百貨(Bourne & Hollingsworth)的帽子,帽子後面拖著飾帶,價值四先令十一便士,還裝飾著天鵝絨和櫻桃。餐具櫥和四輪小馬車擺滿了食物──三明治、香腸卷、果凍、咖啡──全部是自己做的。

愛蜜莉外婆通常會朗誦。她的頭髮豐厚,引人注目,大家都說她真應該去當演員,因為她實在很懂得運用背景音樂以及動作搭配來表達一段獨白。至於其他的家人,歌緹會素描,歌緹的先生奧托會彈鋼琴,而我母親會唱諸如〈我的商隊在何處停歇〉〈灰色雙眸〉〈聆聽水車〉等歌。
大戰爆發之前,誰知道媽咪對人生有什麼期待?我敢說一定是比嫁給一個年紀較長、戴著眼鏡的教書匠要更燦爛輝煌的日子。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每個人的希望與期待,而她在戰爭結束後能夠投入我父親的懷抱已經是很幸運的了。戰後的日子很不一樣,嫁給一個年長的人在當時並不稀奇,因為太多年輕人戰死了。最後她下定決心接受了他的求婚,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成為法蘭西斯‧賽爾菲太太。她在婚禮上穿了飄垂的雙層繡花蕾絲禮服,剪裁寬鬆,腰線低,整體風格走在一九二○年代的時尚尖端。衣料得來不易,因為戰後物資短缺,可她還是想辦法弄到了。她也蒙著面紗,這幅面紗可以追溯到一八六二年,極精緻的布魯塞爾蕾絲,繡著繁複的花朵。那是我父親的姑媽卡爾──莎爾菲夫人的,她在五十多年前的大喜之日也戴過。
說到爹地呢,他當然是穿大禮服,與美麗的新娘的波浪型蕾絲相比,可能太呆板,幸好他在鈕釦眼裡別了朵白色康乃馨,還拄著高雅的「型男布魯梅爾」(Beau Brummell)手杖,鞋面上還覆著耀眼的淺灰色鞋罩。想當年大家真是懂得怎麼樣為婚禮打扮。
法蘭西斯和愛琳共度了四十年的幸福婚姻生活,直到一九六○年,法蘭西斯以八十一歲的高齡去世。兩人度過了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我出生之後經歷了幾次經濟危機,但無論發生了多少波折,似乎都損傷不了他們的快樂。她是一家之主,而他則是完美的紳士。我從來沒看過他們吵架。
他為了佳人能等待那麼久,實在是很感人。也許他的銀行家父親約翰‧莎爾菲離婚這件事讓他心中有芥蒂。約翰的第一任妻子是珂蕾拉‧梅伯利,兩人沒有孩子,而他的第二任妻子蘿拉‧珍‧艾爾溫卻給他生了八個!離婚的前因後果只能任人臆測──珂蕾拉後來也再婚了──不過我覺得約翰可能給了兒子忠告,要他慎防異性的魅力,並且要確定他娶的人是他百分之百愛的人。而在我父親的心裡,那個人就是媽咪,而且只有媽咪。

書籍資訊
《今天永遠比昨天更美麗:英國最炙手可熱90歲名模,寫給你的11堂時尚優雅課》 The way we wore
作者:黛芙妮‧莎爾菲(Daphne Selfe)
出版:大田
日期: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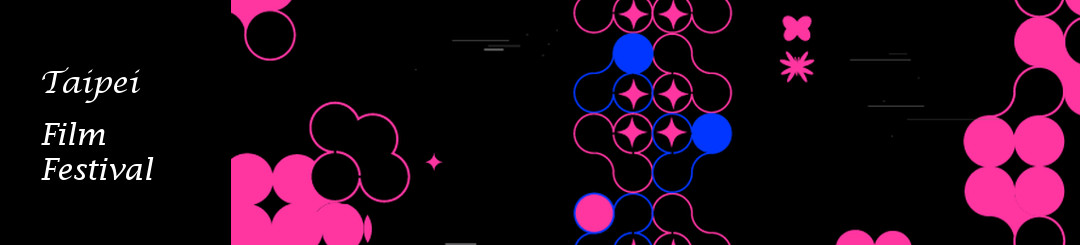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