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當你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你會做什麼?我會去散步;若是幸運,我會發現蘑菇。蘑菇能把我拉回自身五感上,不單因為它們與花一樣色彩繽紛,散發香氣,更因為它們的突然現身提醒了我,光是能在這裡偶遇,就是一份幸運。於是我了然於心,儘管置身在不確定的恐懼裡,依然有樂趣可尋。
恐懼當然存在,而且不只之於我。世界的氣候正在失控,工業進步對地球生靈的影響比上一世紀的世人所想像的還嚴峻。經濟成長不再是發展或樂觀的源泉;我們的任何工作都可能隨著下一次經濟危機而消失。我擔憂的也不只是新災難爆發,我發現,自己還因為缺少故事架構,無從辨認我們正往哪裡走,又為何而去。在過去,臨時工似乎只是倒楣人的命運;但如今所有人的生活卻都這般岌岌可危,哪怕目前我們的荷包還算豐滿。二十世紀中葉北半球的詩人與哲學家們曾因過度安穩而自覺受囚於籠,但現今的我們相較之下,無論位處南、北半球,則是都同樣面臨著無邊的困頓。
我讀過一篇文章,有關蘇聯在西元一九九一年解體時,上千位突然被剝奪國家保障的西伯利亞人跑進森林去採蘑菇。那些雖不是我追逐的蘑菇,卻能證明我的觀點:當我們以為在這受控制的世界裡已一敗塗地,蘑菇自由狂放的生命力卻是一份禮物,也是一條指引。
據說,一九四五年原子彈摧毀廣島後,在一片炸毀的地景中最先復甦的生物就是松茸。
支配原子是人類控制自然這春秋大夢的最顛峰,卻也是該夢想覆滅的開端。廣島的原子彈造成許多巨變。突然間,我們意識到人類有能力破壞地球的可居性,無論是無心插柳,還是刻意為之。這份認知在我們目睹污染、大規模滅絕與氣候變化後更是清晰。現存的不穩定感中有一半與地球的命運有關: 我們能承受何種程度的人為干擾?撇開可續性不論,我們又還有多少能力,能留下適宜居住的環境給後代子孫?
廣島的原子彈也點燃了另一部分的不穩定感,燎燒出戰後出人意表的發展矛盾。二戰後,以美國炸彈為後盾的現代化願景似乎亮晃、璀璨。每個人都從中獲益,未來的方向清楚可辨;但現今還是如此嗎?一方面,遊走世界時,所到之處無不被戰後發展活動建構的全球政治經濟觸及;另一方面,即便發展仍有指望,我們似乎也已喪失了適切的方法。現代化的目的本應是為世界—無論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提供足夠就業機會,而且不是隨便將就的工作,而是享有穩定工資與福利的「典型就業」(standard employment)。這種工作如今相當稀缺;大多數人仰賴的是不規律的生計。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諷刺是,人人仰賴資本主義的鼻息,但幾乎無人從事我們以往所謂的「正規工作」。
與不穩定共存需要的不是只怪罪那些讓我們落此下場的人(雖然那樣看似有幫助,而且我也不反對)。我們可能得環顧四周,觀察這個奇異新世界,可能得拓展想像力,以便掌握它的輪廓。而此時就是蘑菇幫得上忙的地方。在受轟炸的地表上伸展的松茸,有助我們去探索這片已成為我們共同家園的廢墟。
松茸是一種生長在受人類干擾森林裡的野生蕈類。它們就像老鼠、浣熊與蟑螂,能吞忍人類造成的一些環境失調。但松茸不是害蟲,而是價值不菲的珍饈—至少在日本,價位有時高到堪稱地表最具價值的蕈類。松茸因為具備滋養樹木的能力,還能幫助險惡環境裡的林木成長。跟隨松茸,我們就能找到在失調環境裡共存的契機。這並不是進一步破壞的藉口,但松茸確實為我們揭示了合作生存之道。
松茸也照出全球政治經濟的裂痕。過去三十年間,松茸成了全球商品,森林採集的規模橫跨整個北半球,並且要趁新鮮運往日本。許多松茸採集者都是流離失所、公民權被剝奪的文化弱勢者。好比說,在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大多數貿易松茸採集者是來自寮國與柬埔寨的難民。由於松茸價格高昂,因此無論是採自何處,都對生計極有貢獻,甚至能促進文化振興。
然而,松茸貿易與二十世紀的發展夢想卻是幾乎沾不上邊。與我對談過的大多數松茸採集者傾訴的都是無處安身與離散失落的故事。對缺乏其他謀生手段的人來說,貿易採集已經比一般謀生方式來得好。但這到底是何種經濟模式?蘑菇採集者屬於自營,沒有公司雇用,既無工資亦乏福利,只能販售他們私自摘取的蘑菇。有些年甚至無蘑菇收成,採集者只能坐吃山空。野生菇類的商業採集是生計不穩、安全感匱乏的真實寫照。

這本書透過追蹤松茸的貿易與生態,講述生計不穩與環境不定的故事。無論何種情況,我發現自己都被零碎區塊包圍,也就是一種以糾纏的生活方式形成的結局開放的聚合,每推前一步便朝時間韻律與空間軌跡開展的嵌合體。我認為,我們唯有先理解眼前的不穩定屬於全球現象,才能理解當今世界的處境。一旦當局繼續以成長為先決條件作分析,那麼就算時空的異質性在一般參與者與觀察家眼中都顯而易見,專家們也依然置若罔聞。然而,異質性理論仍處於萌芽階段。要察覺與我們現況相關、零碎的不可預測性,就需要重啟想像。這本書的重點,便是要借蕈菇之力催化這一切。
關於貿易:當代貿易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及可能性當中運作。不過,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學者跟隨著馬克思的理論,內化了這種進程,只看得到當下強大的潮流,而忽略了其他。這本書想告訴大家,如何藉著密切關注這不穩定的世界,再加上對財富累積的方式提出質疑,繼而能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避免採納它逐漸崩壞的假設。不強調發展進步的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模樣?它看來可能東拼西湊:財富集中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非計畫區塊產出的價值都已被資本據為己有。關於生態:對人文主義者來說,人類優勢的進步假設強化了視自然為反現代性浪漫空間的觀點。但在二十世紀科學家眼中,進步也不自覺影響著地景研究的領域。關於擴張的假設悄然進入了族群生物學。如今,生態學藉著引入跨族群互動與干擾歷史等新發展,總算能提出有別過往的看法。在這期待漸次落空的時代下,我想尋找一種以變動為本的生態學,許多物種能既不和諧又無需爭奪地共存。
我不願簡化經濟學或生態學的任一方,再說,經濟與環境之間有一條重要且值得提出的關連:那就是在人類財富集中的歷史裡,人類與非人類雙方都被化約成了可投資資源。這種歷史故事一直鼓勵投資人以異化滲透人及物品,也就是使之具備獨立存在的能力,彷彿其他生存上的糾纏再也無關緊要。透過異化,人與物品變成了可移動資產;它們在去除距離的運輸技術下被挪出原有的生活,然後再與其他世界或任一處的資產交換。這種觀點不同於把資產視為生活內涵一部分的看法──例如攝取食物與被食用。在那種情況下,多重物種的生存空間仍然不變,但異化卻消除了生存空間的相互糾纏牽連。異化的夢想鼓吹了地景的現代化,只讓某種獨立資產一支獨秀,其餘的則淪為野草或廢料。此時此刻,去關注生存空間的糾纏似乎成效不佳,或許也過了時。當單獨資產無法再生產,那塊空間便遭廢棄。木材砍光了,石油挖空了,土壤無法再孕育農作物。對資產的搜刮又會從他處開始。於是,簡化過的異化導致廢墟、一塊資產生產荒廢的空間。
這種廢墟如今遍布全球地景,然而,這些地方儘管被宣告死亡,卻仍不乏生命力,廢棄的資產野地有時仍充斥著新的多元物種與多文化生命。在全球不穩定狀態下,我們除了在這廢墟中尋找生機之外,別無選擇。我們的第一步是找回好奇心。去除過簡發展敘事的阻礙,零碎區塊裡的糾纏與律動都等著我們去探索,而松茸正是起點:無論我學到多少,它們總能讓我驚喜連連。
這不是一本關於日本的書,但您往下讀之前需要先對日本的松茸有所了解。由於奈良與京都人經常砍伐山林,以取得木材興建佛寺,並做為鍛鐵燃料,松茸因而在該區域普遍起來。確實可說是人為干擾讓日本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得以興盛,因為它最常見的寄主林木乃是日本赤松,而赤松成長靠的是陽光,以及因森林砍伐形成的礦質土。當日本森林不再受人類擾亂,重新茂盛之後,闊葉林木又遮蔽了赤松,阻止它們再抽芽。
隨著森林砍伐,赤松長遍全日本,被圍簇於蕨類中的松茸也躋身成為珍貴的賜禮,貴族們因此口福不淺。到了江戶時期(一六○三—一八六八),就連富裕的平民,例如城中商賈,也能品嚐到松茸美味。代表秋天的松茸加入了四季慶典的行列。秋季出遊採菇就像春季攜伴賞櫻,松茸也成為詩歌吟詠的熱門主題。

薄暮雪松聽寺鐘,幽山小徑聞秋茸。 —橘 曙覧(1812–1868)
一如諸多日本自然詩中,富有季節感的指涉物總能營造氛圍。除了鹿鳴或豐收月等原有秋色符號,松茸也名列於此。深秋幽微的孤獨感受、懷舊的心情,沾染了些許初冬的荒寒之意,上述詩作便寫出這種氣氛。松茸是屬於貴族的享樂,是得天獨厚的象徵,是得以生活在大自然巧妙中、且追求精緻品味的幸福。也因此,當農人刻意「栽種」松茸(這意思是,當沒有野生松茸可摘時,農人會巧妙地把松茸塞入土中)供貴族出遊摘採,並無人反對。松茸遂成為完美的季節元素,不只在詩歌裡廣受稱道,也在從茶道至戲劇等所有藝術裡大放光彩。
浮雲散盡,我嗅到蕈菇之芳。 —永田 耕衣(1900–1997)
日本在江戶時期終結後迎來明治維新,以及快速的現代化。迅速進行的森林砍伐使得赤松與松茸生長益發容易。在京都地區,松茸成了「蕈類」的總稱,在二十世紀初期更是普遍。然而到了西元一九五○年代中期,情況開始有變。小農們的鄉間林地被夷平,改為林木種植場,為城郊發展鋪路,有的林業地直接遭遷居城市的農人棄置。石化燃料取代了木柴和木炭;農民不再利用剩餘林地空間,這些地方於是長成濃密的闊葉雜林。曾被松茸覆蓋的山坡如今過於幽暗,不利松樹生長。遮蔭過多的松樹也被有害的線蟲侵襲致死。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松茸在全日本已寥寥無幾。
然而,此時又正值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松茸成了奢侈的賀禮、獎賞與賄賂品。它的價格一飛沖天,知道世界其他角落也產松茸,突然變得意義重大。日本海外旅遊者與僑民開始將松茸運回日本;隨著進口商紛紛投入國際松茸貿易市場,非日本的採集者亦群起投入。一開始,有大量不同顏色與種類的蘑菇都被認定是松茸,因為氣味符合。隨著北半球森林裡的松茸聲名大噪,其學名也如雨後春筍般激增。過去二十年來,名字才又逐漸統一下來。如今歐亞地區大多數的松茸都稱作「Tricholoma matsutake」。只是到了北美,該種松茸的足跡似乎只停留於東部與墨西哥山區間。北美西部當地的松茸則被認為是另一品種,美洲松茸(T. magnivelare)。但還是有些科學家認為,以最普遍的「matsutake」來描述這些氣味豐富的蘑菇,還是最為合適,畢竟該物種形成的動態至今仍有待釐清。除非是在討論分類問題,否則本書中也遵照使用這個學名。
日本人已經想出一套為世界各地松茸排名的方法,而且名次也反映在價格上。當一位日本進口商向我解釋排名時,我還真是大開眼界:「松茸就像人,美國蘑菇是白的,因為美國人膚色偏白。中國蘑菇是黑的,因中國人膚色偏深。日本的蘑菇與日本人則是恰到好處地介於中間。」並非所有松茸排名都相同,但這起鮮明的例子能代表分類上以及國際貿易價值上的多變形式。
在此同時,日本人也開始擔心自己會失去這些帶給他們春花漫漫與秋葉瑟瑟季節之美的鄉間林地。因此打從一九七○年代起,志工團體便開始動員,促進林地復甦。這些團體不希望只是消極被動地努力,還期待復原林地的方法也能同時有益於人類生計。高價位的松茸於是成了林地復原的理想成果。
這裡便帶我回到現下不穩定與亂象叢生的生活。生活似乎變得更加擁擠了,不單是因為日本美學與生態歷史,也因為國際關係與資本主義的貿易慣例。這就是本書接著要探討的故事。故而此刻,似乎是得好好認識一下這個蘑菇了。
書名:《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作者: 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18
圖片credit:Eugene Kim@flickr、wiki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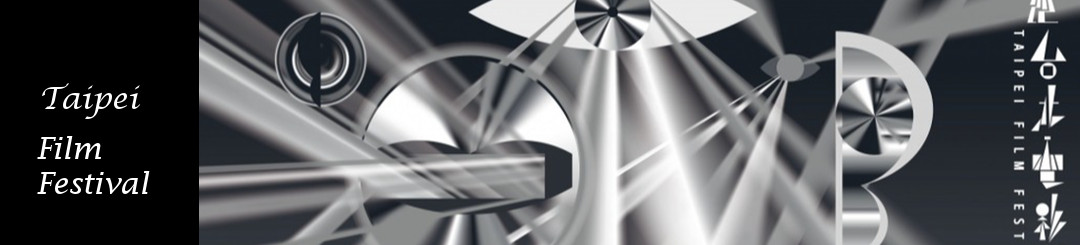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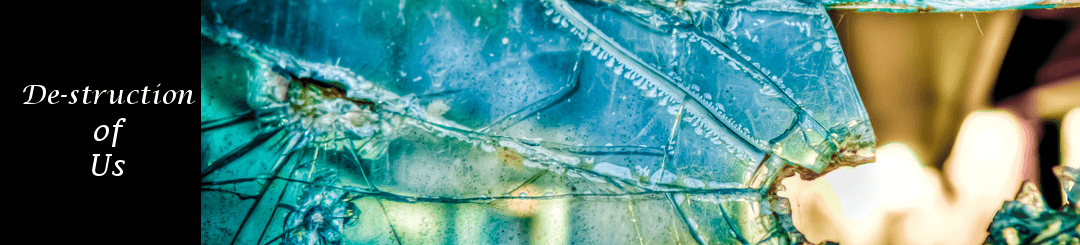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