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伯頓(Huwe Burton)在16歲時向警方承認自己殺害了母親,當紐約警方審訊他的時候,他還處於親眼目睹母親屍體的驚魂未定狀態。經過數小時的威脅與哄騙,他終於說出警方想聽的那些話。伯頓很快便改口否認,因為他知道自己根本沒有弒母,期待司法盡快還他清白。
儘管如此,伯頓仍在1991年被判二級謀殺罪,判處15年至終身監禁的刑期。
伯頓服刑將近20年後假釋出獄,但他永遠無法擺脫被定罪的恥辱。幾個組織的律師團花十多年的時間為他洗刷冤屈,提出與口供互相矛盾的事實,並出示檢察機關行為不當的證據。但對布朗克斯區的檢察官辦公室來說,伯頓的口供遠比其他任何證據都來得重要:畢竟,只有「有罪的人才會認罪」,誰會為自己沒做過的事認罪呢?
2018年夏天,伯頓的律師團請到專門研究審訊技術的法律心理學家索爾‧卡辛(Saul Kassin)為伯頓伸張正義。卡辛指出,虛假認罪(false confessions)的情形並不罕見:近幾十年來,非營利組織「清白專案」(Innocence Project)為365名被告洗清罪名,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因虛假認罪而被定罪。經過30多年的研究結果表明,制式的審訊技術容易將心理壓力加諸在嫌疑人身上,導致無辜的人藉由認罪來逃離這些壓力。此外,年輕人更容易發生虛假認罪的情況,特別是在壓力極大、疲憊不堪和精神創傷的狀態之下,正如伯頓當年的處境。
卡辛的研究讓檢察機關重新審視了訊問與虛假認罪的可能性。不久前,布朗克斯最高法院的法官史蒂文‧巴雷特(Steven Barrett)終於撤銷了對伯頓長達30年的有罪判決。
雖然自DNA鑑定進到美國法庭後,已有數十人洗清因虛假認罪而被定的罪,但伯頓案是司法第一次依據針對訊問所進行的科學分析而改判無罪的案例,認罪口供被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不僅是辯護律師,立法者和警方也連帶開始檢討訊問的方式。卡辛設計的實驗探索了造成無辜者虛假認罪的心理原因。在最近的研究中,他展示認罪(無論真實與否)舉動對證人乃至法醫所產生的強大影響力,並決定了整場審判的走向。

嫌疑人的認罪口供一直是定罪的「黃金準則」。著名的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雨果‧孟斯特伯(Hugo Münsterberg)是第一個注意到這種危險的人,他在1908年提出警告說:「不真實的認罪口供……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但直到1980年代末發生幾起令人震驚的虛假認罪案件後,司法體制才引進DNA鑑定,從而得知虛假認罪所涉及的範圍有多廣,以及認罪口供能起到的作用。
卡辛對此並不驚訝,他花費了數年時間鑽研警方的審訊技術。在堪薩斯大學的博士後時期,他研究陪審團如何做出決定,並被認罪口供的力量所震撼,其影響力實際上百分之百保証了有罪的判決。
他深入瞭解萊德偵訊技術(Rei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警方普遍使用的偵訊技巧)後,他開始質疑嫌疑人口供的真實性。萊德偵訊技術的訓練手冊(目前已經出到第五版)在1962年由芝加哥前警探、測謊專家約翰‧萊德(John Reid)和西北大學法學教授弗雷德‧英鮑(Fred Inbau)首次出版,卡辛說:「讀完後我嚇壞了,裡面使用的手段跟米爾格倫的權力服從研究很像,甚至還更糟糕。」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在1960年代進行了一項社會心理學研究,慫恿受試者對其他學習速度不夠快的人施加電擊。這些志願的受試者並不知道他們對別人施加的電擊是假的,但令人不安的現象是當權威人士指使他們這麼做時,他們還是願意繼續製造痛苦給別人。

萊德偵訊技術剛開始看起來不太一樣。訊問者會先詢問一些問題——有些無關緊要,有些具有挑釁性——進行行為評估,並觀察嫌疑人是否有說謊的跡象,例如東張西望、無精打采或擺出雙臂交叉的防衛姿態。如果嫌疑人被認定為「可能說謊」就會進入正式的第二階段審訊。這時警方會加強訊問的強度——反覆指責嫌疑人,逼他們聆聽案情細節,而且無視所有的否認。與此同時,訊問者還會適時地表現出同情與理解,藉此降低嫌疑人因認罪產生的罪惡感,引導嫌疑人做出認罪口供。
逐步加強力道的訊問與權威人士施加的心理壓力,讓卡辛想到了米爾格倫實驗。米爾格倫是讓一個人去「傷害」他人,而萊德偵訊技則是讓人透過認罪來傷害自己。卡辛質疑,種種的壓力可能導致了虛假認罪的發生。
為了找出答案,卡辛在1990年代初期決定在實驗室與學生受試者一起模擬萊德偵訊技術的場景。卡辛設計了一種名叫「電腦崩潰實驗」的測試,讓學生用電腦進行聽寫,同時也警告他們系統有故障,當按下Alt鍵時就會導致電腦崩潰。當然這是一個謊言:因為無論按下哪個鍵電腦都會崩潰,隨後實驗者會指責學生按下了Alt鍵。
起初,沒有人自願認罪。接下來,卡辛根據警方的審訊技術改良了變異版本。例如警方有時會欺騙嫌疑人,告訴他們犯罪現場有目擊者——讓嫌疑人懷疑自己有沒有正確描述事件(根據美國法律,警方不用對訊問所說的謊承擔責任)。這種手段最知名的案例是:1988年的早晨,住在長島的少年馬蒂‧坦克利夫(Marty Tankleff)準備到餐桌吃早餐時,發現父母被人刺傷雙雙倒在廚房地板上,母親奄奄一息而父親昏迷不醒。警方認為坦克利夫「不夠悲痛欲絕」,因此鎖定他為頭號嫌疑犯。在幾個小時毫無進展的訊問後,一名警探說謊騙坦克利夫「他們已經打給人在醫院的父親,他指控兇手就是坦克利夫」。然而,他的父親其實已經在昏迷中過世。最終坦克利夫在無可奈何之下認罪,直到越來越多的新證據浮現並釋放還他清白以前,他在監獄裡已經服了19年刑期。
卡辛永遠無法在實驗室裡模擬出這種創傷,但他可以在電腦崩潰實驗中設置類似的變數:在實驗進行中,安排一名目擊者指控學生按錯鍵。實驗結果顯示,被目擊者指控的學生的認罪比例是沒有目擊者指控的兩倍多,幾乎每個面對偽證指控的學生都認罪招供。有一些學生以為他們真的按錯鍵,急急忙忙解釋說出如「手的側面不小心壓到別的按鍵」的理由。他們深深將自己的罪惡感內化,以至於當卡辛告訴他們真相時,有些人還不願意相信。

還有一種情況是警方沒有捏造手中握有證據的謊言,但卻暗示嫌疑人很快就會有新的、可構成犯罪事實的證據出爐。舉例來說,訊問者可能會告訴嫌疑人目前正在等待犯罪現場的DNA化驗結果。這種說法看起來會讓無辜者更強烈地否認犯罪,畢竟新證據出來馬上就能擺脫嫌疑。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卡辛採訪後來被證明無罪的人的說法,他們認罪往往只是為了逃離當下巨大的心理壓力,相信新證據之後也會為他們洗清罪名。但不幸的是,嫌疑犯既然都已經親口認罪,這些所謂的「新證據」在司法系統面前也變成參考用的東西。
卡辛在電腦崩潰實驗的另一個變異版本中,測試了警方所慣用的「虛張聲勢」技倆。這一次實驗者除了指責學生之外,還告訴學生伺服器上面有按鍵紀錄,等等就會開始一一檢查。結果顯示,當這種說法出現後,虛假認罪的比例大幅飆升。實驗後的問卷表明,許多被「虛張聲勢」嚇到的學生就像卡辛所採訪的那些人一樣,同意在一份認罪書上簽字只希望盡快離開房間,內心假設伺服器紀錄最後會還他們清白。卡辛表示,從這方面來看,相信自己的清白與過度相信司法體系本身相當危險。
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家多年來重複進行類似的電腦崩潰實驗,也都得出類似的結果。批評者經常對卡辛的研究提出質疑,認為他的實驗對象被指控的「罪行」只是粗心大意或無意間犯下的行為,而且認罪也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不過,其他研究的結果已經反駁了大部分的質疑。羅傑威廉士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梅麗莎‧羅薩諾(Melissa Russano)設計的實驗要求參與者解決一系列的邏輯問題,有些透過小組合作,有些則獨自完成。實驗者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學生都不能協助必須獨自完成的項目。然而在此之前,部分的學生參與者被要求表現出很沮喪的樣子,促使不知情的參與者違反規定去幫助他們。
在這些實驗中,違反規定幫人作弊的參與者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犯罪」,而違反校規的作弊行為,也會讓認罪帶來嚴重的後果。但就像卡辛所發現的那樣,指責性的訊問還是會產生虛假認罪的情形。羅薩諾也測試了標準訊問的常見手段:降低嫌疑人對於認罪的罪惡感,她會告訴參與者:「你可能不知道,認錯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這類型的話術讓虛假認罪的招供率提高了35%。
萊德偵訊技術的大部分技巧包括觀察說謊的語言和非語言跡象,有很多警察以為自己特別擅長讓罪犯招供。十多年前,卡辛就對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自信心進行檢視。他找來非常擅長說謊的人(麻州監獄的一群囚犯)給他們一小筆錢演戲,要求其中一半的人在影片裡說出自己的真實罪行,另一半人則隨便說些別人犯下的罪。然後他把影片拿給大學生和警察看,結果發現兩組人都沒有特別擅長查明真相(一般人大概能猜對一半),而且學生的表現甚至比警察還要好。然而,警方仍然對自己的「觀察能力」沾沾自喜,對結論無動於衷,卡辛說:「這是非常糟糕的結合,訓練讓他們的觀察能力變得不那麼精準,同時又自信過了頭。」

卡辛辦公室的海報上展示了28張臉孔,上面包括男性、女性、成年人、青少年、白人、黑人、拉美裔,他說:「看看這張海報有多少不同類型的人——所有的人類。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承認犯下不屬於他們的罪,沒有特定的人會做出虛假認罪,因為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認罪有時甚至會推翻沒有瑕疵的DNA證據。1989年,五名青少年在經過數小時的訊問後認罪,他們承認在紐約市區毆打並強姦了一名慢跑的女子。儘管他們很快就改口否認,而且從受害者身上提取的DNA也不屬於他們,但在檢察官解釋了供詞與證據的矛盾後,兩個陪審團都判他們有罪。檢察官提出了一個推論認為還有第六個身份不明的同夥也強姦了受害者,然後這個同夥是唯一一個射精留下DNA的人,這種「身分不明同夥」的推論也經常被用於其他的虛假認罪案件。13年後,與DNA樣本相符的男子(一名被判終身監禁的連環強姦犯和殺人犯)承認當時是他獨自犯案。
這麼不公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呢?卡辛在2016年發表了另一項研究,研究團隊以模擬陪審團的實驗來還原這種情形:他們詢問受試者會選擇相信「供詞」還是「DNA證據」時,受試者會選擇DNA證據;但是,如果檢察官提出一個推論來解釋DNA證據為什麼跟供詞互相矛盾時,人們會壓倒性地選擇站在供詞這一邊。
卡辛和幾名同事共同撰寫了一份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白皮書,警告不當的審訊存在嫌疑人被脅迫的風險。他們建議進行幾項改革,例如禁止警方說謊誘導嫌疑人、限制審訊時間、從頭到尾記錄審訊過程,以及禁止使用降低認罪罪惡感的話術。他們還表示,希望嫌疑人自己做認罪口供的做法本身就具有瑕疵,因此有必要「徹底重新構思」這些審訊技術的正當性。
參考報導: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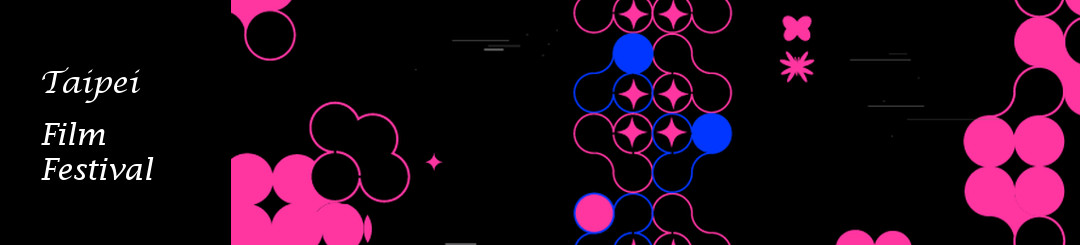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