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今(2019)年六月十八日為當代法政耄學哈伯馬斯九十大壽,學界陸續紛作文章致敬。〈一個議論的共和〉原為Raymond Geuss 刊載於德國哲普網站 Soziopolis 一文,之後以英文改寫並在《The Point Magazine》雜誌出刊。Geuss批評哈伯馬斯對公共議論的理解實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激起當代哲學人如Martin Jay、Michael Quirk、Seylia Benhabib一番論辯,尤其是與Seylia Benhabib一來一往的論戰。本文摘譯自Raymond Geuss 英文文章。

文|Raymond Geuss
「議論」真的那麼美好?「溝通」真的存在?那麼,如果我說並非如此呢?
對於脫歐的公共議論,已對英國造成不計可數,甚至可能是無法回復、完全泛濫的損害。顯而易見地,投票前的「議論條件」(conditions of discussion)根本就並不「理想」(ideal)。雖然沒必要再花精力說明,不過大家應該還記得十年之前除了一群狂熱份子外,根本沒有人真的有興趣去議論對歐盟的關係。這些人當時不在檯面上,也沒造成什麼損害。
過去四年來的議論,只是一些報社老闆(他們很多根本就沒設籍在英國)、一小群有錢的柴契爾主義餘黨、跟某些政治機會主義者興致昂然在煽風點火。那些死硬恐歐派本來不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只有在公共議論的過程中,這些先前看來為不足道的少數意見,可以取得政治代表權表達出對歐盟的質疑。接著,相當偶然的歷史因素使得另外百分之十七的人參加脫歐投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些脫歐的倡議者說服人民誤以為,這些西敏寺的政治人物捅出的麻煩,是布魯塞爾官僚直接導致的結果。過時的結構性問題,跟可笑的「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選舉制度,使得本來才佔選舉人口中百分之三十七者,能成為有政治效能的,也就是時常提及的,單次選舉達投票率中百分之五十二贊成脫歐的結果。現在則成為三年來「人民勢不可擋之聲」(Irresistible Voice of the People)的勢力。
諷刺的是,過去兩百年來大聲疾呼反對盧梭共和理念,現在則突然轉向的保守黨,卻完全敗給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 )這種主張脫歐的托利黨人。一連串怪奇的意外,像是英國首相的墨守成規、爛到立下典範的無能,使得佔選舉人口才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真正成為脫歐派;毋須贅言,無論情況怎麼理想,也無法在短時間得以改變。而且無論是出自什麼原因或是什麼意義之下,就明顯的心理原因而言,一個人要取得公共位置,就不會亟於承認曾經犯下的錯誤。議論雖然非中立的,但卻能改變現狀。無論先前決定正確與否,只要政府因應再次失敗,就會又改變現狀,然後造成節外生枝的怨懟,把問題弄得更麻煩。以最近流行的術語來說,許多投票贊成脫歐的,變成了一種身分認同(identity)。
當我跟這些脫歐派對話時,我並不會假設哈伯馬斯「更佳論理的力量」(power of the better argument)如此天經地義,而且很確定的是,那種假設理想環境下無邊無際的議論,就能免於認知跟道德扭曲下帶來的不適,還能最後達到彼此的共識,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種假設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相較於訴諸身分認同,論理顯得無效。十九世紀的齊克果就很熟悉這種現象,而且他花了很多精力去用哲學來理解跟解釋它。「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並不希望跟歐洲人混為一談,因為我們就是蔑視他們。」當有人說這種話時該怎麼辦?只有長期的社會政治轉型、由外對內發生影響的事件、跟受到關注的持續政治擾動,才有機會產生效果。長遠看來,就如凱因斯清楚明示的,我們都完了。
在其著作《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開宗所言,阿多諾對於「在任何地方、對於任何人的任何想法,都可放諸四海皆準地溝通,這類自由主義的虛構」有很沉重的保留;阿多諾批評政治自由主義,以及溝通作為哲學的基本組成之原則,不過他對自由主義跟普世溝通的拜物教之敵意,卻不受到其他法蘭克福學派學人的護持,甚至是下一代開始嶄露頭角之前就已棄絕;即便在1970年代初,如今已九十歲的哈伯馬斯,在當時仍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非正式接班人時,就已開始重新導入新康德主義版本的自由主義了─用「論辯」(discourse)這個相當引起激論的概念,來解釋他所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之所以是新康德主義的:其一,就如同康德著重是否在合乎「法權問題」(quid juris?)而非「事實問題」(quid facti?),哈伯馬斯重視的是正當性(legitimacy)的哲學問題;其二,就像康德一樣,哈伯馬斯執著的是,得以自然生成出規範性的不變歷史「結構」─對於康德是理性的,而哈伯馬斯則是溝通的;最後,康德癡於清楚強烈的二分法─對於截然不同的領域,像是道德與審度、先驗跟後驗,對彼此之間可能的越線則感到深刻焦慮。這類康德式的二分法,也反映在哈伯馬斯對論辯與工具行動之間的對立設定。這種普世溝通的自由主義虛構,阿多諾就視之為一種病態,但哈伯馬斯則從來就不試著與之保持距離,而是積極擁抱之:哈伯馬斯的自由主義是從先驗的溝通理論中找到基礎,如果真的有這種東西的話。
就哈伯馬斯而言,溝通並不是簡單的經驗現象,而是從西方歷史所建構出的主要意識形態─如自由、民主、法權等─而來的雙重結構。一方面,溝通一詞,經驗上在日常生活使用中毫無問題,而就潛在的意識形態施用,則是人類生活中毫無疑問、不證自明的基本要件;另一方面,溝通結構實際上是哈伯馬斯用來指出行動者的溝通處境──德文的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因為將兩者截然不同的「語言理解」跟「道德同意」混為一談,不但在翻譯成英文時實在容易混淆,也是造成更大誤解的來源。單就一個德文字詞,就在論理上輕鬆做出語言學的抽換概念。如果哈伯馬斯曾反思過這問題(雖然我並不認為他有):假定日常的德語使用是在前理論的方法中表達出,理解與規範性之間有固有連結的基本真理。而(用相當不明確的方式)來承認,這一般來說是正確的,當然不一定就是為哈伯馬斯這方面的連結來背書:認為言說就是跟言談對象承諾達到(理想上的)道德同意,只有受到導往理想上道德同意的言說形式,才是全然意義上的溝通,也就是「溝通行動」。而就溝通而言,一方面是經驗的,另一方面則是感知跟完全規範意義的,兩者之間則可能是意識形態扭曲的遊樂場;很弔詭地,對哈伯馬斯而言,社會中的溝通並不是溝通行動,而是「扭曲」到無法服膺於溝通自身隱微的規範;以至於如何在社會強制下(扭曲的)虛假溝通,跟免於任何社會宰制形式的言說行動之間區分,這則是重要的。如何清楚劃分出虛假言說跟真實言說之間的界線,而且從不混淆,就跟對康德劃清「義務」跟「喜好」、「經驗驅使」跟「道德律令」般,對哈伯馬斯一樣重要。
自然而然,這類理論跟傳統自由主義的特定動機之間的關聯,實在太需要議論了。畢竟,對於「自由議論」(free discussion)理念的高度重視,是傳統自由主義中貨進貿來之一部分。肯定的是,哈伯馬斯在持續推展的過程中也遇到傳統自由主義者需面對的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是,儘管他們不大承認卻也不大會留意的,自由主義看似預設議論總是可能的、而且理所當然是良善的──只要不是在攸關生死危難之際,一般而言,自由主義者願意提出的龐大理想假說。其中一種挑起自由主義跟特定宗教狂熱份子之間對立的論調是,早期基督徒等宗教狂熱份子般,總是相信所有人類生活的處境都是緊急危難之時,因為末世近了,審判將是無情的,而後果則是永恆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一個默認的假設是,自由跟不受限的議論總是有助於澄清解決問題,也就是說,至少「原則上」總是有達成共識的可能。彌爾有個惡名昭彰的想法即是,自由主義不是給未開發國度的,這也就是預設了印度人只能接受在大英帝國的慈愛統治之下,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很難公開反對自由議論的理念。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認知到這些假設都是在經驗上謬誤的。議論,即使是在合理有利的條件下,也不需要啟蒙、澄清、或是導向於凝聚共識,而是實際上只需要凝聚爭端,而且激發進一步的譏諷、怨懟跟分裂。想想脫歐吧!只要我知道越少關於他們真正的想法跟感受,我就越能跟他們處得好。任何在真實世界有議論經驗的人就知道,議程的哪裡其實都到不了,最後然後只能慢慢中離,讓新加入的外人更加困惑,以至於意見越來越強硬,各方之間越來越嚴峻對立。議論越長則越激烈,也就越糟。這就是哈伯馬斯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受到激勵鼓舞,提出以「理想的言說處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場所,來做為排除這些困難的工具。儘管如此,這並不就代表任何言說者都必須「預設」目前的處境要在理想的言說處境下評估,也不是說在如此理想的處境下就必須達到共識。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也就是哈伯馬斯開始寫作之前半個世紀,美國哲學家杜威也發展出溝通理論。肯定的是,相較於哈伯馬斯,他很清楚強調溝通作為「自然主義的過程」(naturalistic process),而且以只有人類「行動」(action)能夠帶來澄清跟解決方案為前提。任何的澄清是用來回應既定處境及其一系列問題等等,除非得到特定的修正,否則仍舊保持與既有結構的關聯;而只有更進一步的行動,特別是特定的抽象行為(acts of abstraction),可以轉化成某些更為普遍的應用。在有些,但非全部的處境,相關行動可以採取議論形式,但議論形式並不一定就設定為先驗理想的。如果議論沒有用,那就一如往常地必須出面干涉;就此,干涉並不見得是那麼理所當然地受到歡迎,更可能就是直接出手,而不是基於某種天人感應。這對很多人而言實在是不好說,甚至是褻瀆自由主義的原則。不,當然,對於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而言,必要時候就是要用非常手段,特別是像彌爾以及東印度公司要保護自家利益時,雖然他們不大願意承認這點。
就分析哲學之中,相襯自韓波「我即它者」(je est un autre)的是,蒯因的「基進的翻譯是從家開始」(radical translation begins at home)。即使如此,蒯因指出:從對話內底,我的靈魂即指導自身,我面對的是操著全然陌生且模糊語言的講者。語言,也必須「翻譯」,而且能夠完成翻譯的唯一根基是講者的行動─取決於對我而言是否看得見或可近用的─也就是說,我跟自己對話的時候,取決於與我說話的那個人的行動。如果,那麼,我並不處於與我自身規範理解(我們又回到德文字詞Einverständnis,跟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同源)的完全透明關係之中,而且如果這是真確的,根據蒯因所言,那麼就如此狀態的概念則是不一致的。那麼,就哈伯馬斯就政治的規範性理解跟真正共識,我們到底是在自嗨什麼呢?
沒有多少能夠讓我們得以在自然現象中的「溝通」建立起安全地帶,而真正完全豁免於可能來自四面八方武力的使用;抑或,我們也無法在現實當中,實現某種烏托邦意義上豁免於宰制關係的溝通形式。即便如此,如哈伯馬斯所說,言說的「內在邏輯」(inherent logic)「指涉」(implies)有某種免於宰制的自由,任何「特殊」(particular)的理論試圖指出它絕緣自歷史,而且真實存在的溝通形式最終會只是讓某些我們當今情況中偶然的樣態變得絕對。歷史前車之鑑是,康德的論證就好似隨著人類理性自身以降的需求,是有利於十八世紀的死刑跟反對自殺權利的。

就哈伯馬斯依此脈絡所提出「當代主要的問題是缺乏社會機制的正當性,而且可以藉由發展溝通理論得以紓解」之論題,有個很好的理由懷疑:首先,如先前所提,這是把「正當化」當作哲學基本問題,甚至是當今哲學基本問題的一種康德式偏見,而且也不大會當作是現在世界的基本社會問題。那麼,哈伯馬斯「沒有宰制的溝通」(discourse-without-domination)的概念就沒有意義:溝通並不是穩定不變的結構,也絕對不是那個讓我們得以從中推斷出一套普世有效的規範、以及對所有宰制形式認同與批評的。換言之,並沒有那種溝通,是必然來自箇中隱微的普世規範,而且可予以、一直藉由參與此行為形式者所預設、卻可不受規矩主治的語言行為形式的。
早期自由主義的神學基礎(如史賓諾莎、洛克等)在十八世紀後期就分崩離析。因此,兩百年來(從貢斯當、洪堡、彌爾、到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者,一直試圖不訴諸上帝及其依附的神學概念也能論述。自立、沒有神學為底的自由主義看似歷經長久的實驗,但實際上這短暫的成功也只是端賴於殖民強權如大英帝國及其後繼者之手。如果帝國夠大、夠強、夠有自信的話,就讓自身在一定限度內,理所當然地捍衛容忍、言論自由、多元意見,甚至保衛某些公民權利。古老的帝國秩序,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全然道德崩壞;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動山搖,則意味著美國帝國提供一個歐陸大小的露天動物園給這些自由人(homo liberalis)的各類亞種,來安內庇護其殘存餘勢。自從九一一事件跟2008年九月的經濟危機,這點空間也在我們眾目睽睽下緩慢崩解,像是目睹川普總統正在實行尼采的格言:給已經墮落的,補上一腳。
晚期自由主義的溫柔憂懷情調,滿溢著哈伯馬斯帶有特定歷史大時代感卻又沒什麼新意的書寫。1945年之後,不斷提及中歐如何受到政治經濟社會的重構問題,但很殘忍的是,所提的替代方案,不是整併到西方世界,不然就是到東方世界,卻沒有更為基進的建議或嘗試的可能。將德國民主共和國整併到西方世界,早在1970年代就是煮成熟飯的事實(a fait accompli),當時哈伯馬斯的著作剛嶄露頭角,但之後1981年才出版的《溝通行動理論》在當時仍是初步的雛型。黑格爾曾說過,哲學總是跟在事實之後,而這也是如此:類先驗的哲學奉對話為公共理性的重要媒介,而藉由強烈加諸在德國的康德式藍圖,來結合像是在英國、荷蘭、美國跟法國強烈的自由主義傳統,為「西方整合」(West integration)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
杜威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幾乎能在「實用主義」(pragmatism)、「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等字詞之間抽換──也沒什麼能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取得可能形塑的立足點。太多人一聽到政治或是社會實驗就感到驚慌,對這完全理解的是,對法西斯實驗復辟的恐懼,以及面對「東方偉大文化實驗」(亦如佛洛伊德「一個幻覺的未來」)的焦慮。「拒絕實驗!」就是很有效的口號,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大致可類比於美國民主黨)曾在1950年代後期拿來用過。然而,儘管東歐的負面範例,不容忽視社會主義的某些面向仍舊受到歡迎,而且在1960到1970年代之間越來越明顯。那麼可想而知,持續處理掉可能的「實驗」,不只是公開的政治手段,也可能是迂迴地從議論空間中排除,確保完全不會受到議論。波普就擺出一種姿態,指「太大規模」的實驗違反「科學研究的邏輯」,而杜威則指出沒有什麼是不變的「科學方法」或是「研究邏輯」,因為科學最重要的面向就是,只要有在進步,研究方法自己就會變。弔詭地,哈伯馬斯在這脈絡下,也是跟波普站在同一陣線的,特別是在他提出理性溝通有先驗的限制之下,也就排除掉那些認為是「無法議論」的特定「工具性」政治干預的可能。那麼,它的先驗主義就不會是受到體面教育的哲學家拿來的華麗裝飾,而是為哪些是可以議論的、哪些是不受歡迎的題目,來做為劃地設限的不可或缺工具。對議論的限制,並不只是在德國而已,而在美國的羅爾斯,實際上也從康德的高尚雜貨店借了一點貨,來試圖保護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受其他認為太基進的替代方案破壞。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我們生活在最好的」如此愚蠢的說法,卻不是維持現狀的最佳辯護。更有效率的做法是隱藏起來對既定社會經濟結構的肯定,卻以一家之言鼓吹得以批判各種個體缺陷、不足跟不適。「話語批評」(discursive criticism)的意識形態,在於建構自身的更好機會,因為它給予了採用的人有特定的心理優勢,也同樣適用於吸收、導向跟疏通可能失控的能量。這歸功於康德,對於目前不滿的情緒,只要一小撮歸咎於個體不完美跟社會系統的「改革式批評」,就會雲消煙散。
哲學家並沒有預言家那種稟賦。難以避免地,人們一方面是思索未來,另一方面則是思考它的運行法則,那麼,也可能懷疑下一代年輕人是否能像1950到2000年的人們一樣專注執著在議論上。如果最後是跟前人幾無二致,但有著不同的價值觀、欲望跟取向,那麼有什麼樣的理由又可以反對議論?是因為背叛了某些自由議論的理念?那就算他們真的背叛了,那又有誰可以責怪他們?
攝影者:Gorka Lejarce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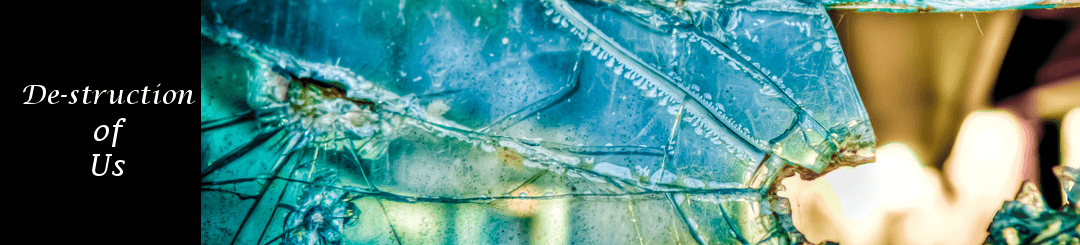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