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Nicole Krauss
譯|施清真
我和索拉雅已經三十年沒有見面。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試圖打聽她的下落。我想我不敢見到她,我生怕年歲漸長的我會想要了解她,說不定甚至看懂了她,換言之,我生怕看懂了我自己,不願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種種。時光荏苒,歲月流逝,我愈來愈不常想到她。我上了大學、讀了研究所、比我料想中較早結婚、接連生下兩個女兒,就算索拉雅曾經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各個影像也只是接二連三地一閃而過,有如水銀般迅速揮發,而她同樣瞬間再度消散。
我十三歲之時遇見索拉雅,也就是我們家出國待在瑞士的那一年。要不是我爸爸已經擺明告誡大家「誰都別相信、誰都得懷疑」,我們說不定會將「做出最壞的打算」奉為家訓。我們家在懸岩邊,但房子相當壯麗。我們是歐洲猶太人,即使在美國也一樣,換言之,我們這種人曾經遭逢種種浩劫,未來或許也是劫數難逃。我們爸媽吵得很兇,兩人的婚姻始終瀕臨破碎。家中的財務也前景堪虞;我們已被告知這棟房子即將出售。我們沒有任何收入,因為我爸爸跟我祖父經年累月扯著嗓門對罵,直到我爸爸終於從家族企業出走,再也不願天天跟我祖父幹譙。我爸爸重返校園時,我兩歲,我哥哥四歲。他先是攻讀醫學預科,然後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院,畢業之後在「特種手術醫院」的骨科實習,但何謂「特種」,我們並不曉得。在那七年的受訓生涯,我爸爸時時值班,在急診室待了無數個夜晚,見識了形形色色傷勢慘重的患者:汽車相撞,摩托車事故,甚至空難事件——那架飛往波哥大的哥倫比亞航空飛機驟然墜毀於長島科夫內科村時,我爸爸正好在醫院值班。心情沉到谷底時,他搞不好緊緊依附著心中的迷信,試圖相信倘若自己夜夜與驚恐對峙,說不定家人們即可躲過一劫。但在他擔任住院醫生的最後一年,我祖母在一個下著大雷雨的九月午後出了車禍,一部超速的貨車在第一大道和第十五街的轉角撞上她,造成她顱內出血。等到我爸爸趕至貝爾維醫院,他的母親已經躺在急診室的擔架床上,她捏了捏他的手,漸漸陷入昏迷,六星期之後就撒手西歸。她辭世不到一年之後,我爸爸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將我們全家搬到瑞士,開始接受創傷醫學的訓練。
綠草如茵、井然有序、確保中立的瑞士居然設有世界一流的創傷中心,似乎顯得矛盾。當年那段期間,瑞士全國上下瀰漫著有如療養院或是精神病院的氛圍。但環繞四周的並不是加裝軟墊的高牆,而是皚皚的白雪,白雪捂住了聲響,軟化了一切,數百年下來,瑞士人因而不加思索地逕自怯言。但說不定這就是重點所在:只有一個執意於監控預算、從眾一致、產製鐘錶、火車從不誤點的國家才佔盡優勢,有辦法處理肢體遭受重創的緊急狀況。瑞士也是一個多語系的國家,這倒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意外,讓我和我哥哥暫且忘卻家中的陰沉與紛爭。我爸爸受訓的機構在巴賽爾,隸屬德語區,但我媽媽認為我們應該持續學習法語,更何況瑞士德語幾乎就是德語,我們的外婆就是講德語,而她整個家族都遭到納粹殺害,不消說,任何事情只要跟德國沾上一點邊,我們都碰不得。所以我們就讀日內瓦的國際學校。我哥哥在學校住宿,但我剛滿十三歲,不符合住宿的標準。為了讓我免於承受德語引發的心靈創傷,爸媽幫我在日內瓦的西郊找到落腳之處,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搬進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家,成了她家的寄宿生。艾德菲爾德太太是個英文代課老師,頭髮染成稻草黃,臉頰紅通通,彷彿自小就習於濕冷的氣候,但不管怎麼說,她依然顯老。
我的小臥室有一扇窗,看出去就是一棵蘋果樹。我搬進來的那天,鮮紅的蘋果掉了滿地,在秋陽下漸漸腐爛。臥室裡有一張小桌子、一把閱讀椅、一張床鋪,床尾擱著一條折疊起來的軍用毛毯,灰色的毛毯非常陳舊,說不定二戰期間就已供人使用。褐色的地毯已經磨得脫線。
另外兩位寄宿生都已滿十八歲,共用走廊盡頭的臥室。我們那三張狹小的床鋪都曾歸艾德菲爾德太太的三個兒子所有,但他們已經長大成人,早在我們使用這些床鋪之前就搬了出去。家中看不到他們的照片,所以我們始終不知道他們的長相,但我們幾乎從未忘卻他們曾經睡在我們的床鋪上。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兒子們雖已離家,但他們和我們睡過同一張床,這樣的連繫想來有點淫蕩。艾德菲爾德太太也從沒提過她的先生,說不定她根本沒有結過婚。她不是那種樂於提及私事的人。就寢的時間一到,她默默關掉我們的電燈,連句話都沒說。
入住這棟屋宅的頭一晚,我隨同那兩個年紀比我大的女孩坐在她們臥室的地板上,身邊堆滿了她們的衣物。她們在家裡使用一款名為「黑色達卡」、價格低廉的男用古龍水,古龍水濃烈的香氣滲入她們的衣物,散發出一股我不熟悉的氣味。她們的體溫和獨特的膚質淡化了這股氣味,但她們的床單、隨手脫下的襯衫、隨身攜帶的包包依然不時散發出強烈的古龍水味,艾德菲爾德太太甚至不得不開窗透氣,冷風一吹,所有氣味再度隨風而逝。
我聆聽那兩個大姐姐閒聊她們的生活,字字句句有如密碼,令我不解。她們譏笑我不懂世事,但她們對我都非常和善。瑪莉來自曼谷,先前住過波士頓,索拉雅來自巴黎十六區,先前住過德黑蘭,她爸爸曾是皇家工程師,趁著革命之前帶著家人流亡海外,走時匆忙,來不及把索拉雅的玩具打包,卻已及時轉移大多資產。她們跟男孩子上床、濫用藥物、違抗父母與師長,行徑一再失控,致使兩人不得不到瑞士多讀一年高中,而在此之前,她們壓根兒沒聽過所謂的「十三年級生」。
◆◆
我們經常摸黑出門上學。走到公車站的途中,我們必須穿過一片田野,十一月間,田野已經覆滿白雪,枯黃乾硬的葉桿有如剪刀般冒出雪地。我們總是遲到。我們三人之中,始終只有我吃了早餐,始終有人的頭髮未乾、髮尾結了薄冰。我們冷颼颼地擠在公車站旁,吸著索拉雅的二手菸,等候下一班公車。公車載著我們行經一座亞美尼亞教堂,來到橘色的電車站,然後車程漫漫,把我們載往市區另一頭的校區。我們各有課程表,下課的時間不一樣,所以回程各自搭車,只有開學頭一天、在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堅持下,瑪莉和我相約一起搭車返回寄宿家庭,但我們搭了反向的電車,結果被載到邊境另一頭的法國。摸熟路線之後,我經常在電車站附近的書報攤逗留片刻買糖果,然後繼續轉搭公車,糖果擱放在開敞式的罐筒中,我媽媽總說那些糖果沾滿陌生人的細菌。
我從來不曾如此開心、如此自由自在。不單只是因為我逃開我那個陰鬱焦躁的家,更因為我不必再見到我那群小裡小氣、荷爾蒙作祟、殘酷得無以復加的高中同學。我年紀太輕,沒有資格考駕照,所以先前始終無處可逃,只能一頭鑽進書本,或是在我們家後面的森林裡走走。現在放學之後,我可以在日內瓦閒逛數小時。我始終沒有特定方向,但我經常走著走著就來到湖邊,觀看遊湖的船隻來來去去,或是幫我看到的遊客們編故事,尤其是那些坐在湖邊長椅上卿卿我我的情侶。有時我到H&M試穿衣服,或在舊城區四處閒逛,「宗教改革紀念碑」時時吸引我的目光,我非常喜歡那座威武高聳的石牆和牆上各個清教徒偉人的浮雕,我不識其名,只認得約翰・加爾文,當年我還沒聽過波赫士,我的生命與這位知名的阿根廷作家也還沒有任何交集,我不知道他一年之前剛在日內瓦辭世,也不知道他曾致函他的友人,信中聲稱他在日內瓦始終感到「莫名的欣喜」,同時闡述自己為什麼希望長眠於這個他客居的城市。多年之後,朋友送我一本波赫士的遊記《圖片冊》,書中有張巨幅的照片,照片中赫然是那幾座莊嚴肅穆、我年少之時經常造訪的偉人浮雕,令我大吃一驚。偉人們全都反猶太,堅信宿命論,認定天主握有絕對主權,照片之中,約翰・加爾文微微前傾,凝神俯視失明的波赫士,而波赫士拿著手杖坐在凸出的石塊上,下巴微微上揚。照片中的加爾文和波赫士,一人俯視,一人仰望,彷彿暗示著協和與默契,我跟加爾文之間稱不上有何默契,但我也曾坐在那個石塊上抬頭看著他。
在市區閒晃之時,有時會有男人用法文跟我搭訕,或是睜著眼睛不停打量我。這些偶遇令我難為情,在我心中留下一絲羞愧。這些男人通常是非洲人,笑容可掬,一口燦燦的白牙,但有次我站在一家巧克力專賣店前面觀賞櫥窗,一位歐洲男子從我身後走過來。他穿著一套體面的西裝,悄悄趨前,臉孔幾乎貼上我的頭髮。他操著微帶口音的英文在我耳邊悄悄說:「我一隻手就可以把妳折成兩截。」說完之後,他繼續前進,神態極為冷靜,腳步極為平穩,好像船隻航過無波的水面。我一路跑到電車站,上氣不接下氣地站著等車,直到電車進站、吱吱嘎嘎地停下,我如釋重負地上車,頹然癱坐在司機後面的座位上。
我們六點半就該準時上桌吃飯。艾德菲爾德太太座位後方的牆上掛著一幅小小的山景畫,直至今日,我一看到油彩繪製的小木屋、頸間掛著鐘鈴的乳牛,或是身穿格布圍裙採集野莓的山間小女孩,依然始終聯想到烤魚和水煮馬鈴薯的香味。用餐之時,大家很少交談。但說不定這只是因為我們在樓上的臥室裡聊了好多,相形之下,用餐之時的對話似乎不值得一提。
瑪莉的爸爸入伍從軍、駐派曼谷之時結識她媽媽,他把她帶回美國,幫她買了一部凱迪拉克轎車和一棟馬里蘭州的平房,兩人離婚之後,她媽媽返回泰國,其後十五年,瑪莉往返於爸媽之間,成了兩人爭奪的目標。她最近幾年都跟她媽媽住在曼谷,交了一個非常愛她、非常會吃醋的男朋友,她經常跟他上夜店跳舞、喝酒嗑藥、瘋一整夜,她媽媽無計可施,自己又忙著交男朋友,於是跟她爸爸提及這個狀況,她爸爸聽了大怒,喝令她離開曼谷,把她送到以女子「精修」學校著稱的瑞士,這些學校專擅修飾狂野不拘的女孩,磨去她們不雅的稜角,把她們捏塑為儀態優雅的淑女。「日內瓦國際學校」不是這種學校,但瑪莉既然已經超齡,沒辦法進入一所合宜的女子精修學校就讀——在這些學校的估算中,她業已成形,無法再被捏塑——於是她被送進「日內瓦國際學校」,在這裡多讀一年,完成她的高中學業,成了所謂的「十三年級生」。除了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家規,瑪莉的爸爸還嚴格規定宵禁時間,瑪莉偷喝艾德菲爾德太太的料理專用酒之後,這些禁令更是嚴苛。因為如此,所以在那些我沒有搭火車回去巴爾賽探望爸媽的周末,瑪莉和我經常一起待在寄宿家庭,索拉雅則經常外出。
索拉雅不像瑪莉一樣讓人覺得喜歡惹事生非。最起碼她不會輕率任性地惹麻煩,也不會一時衝動,不計後果地跨越旁人設下的界線或限制。如果非得說些什麼,索拉雅其實散發出某種權威感,好像打心眼裡就敏銳細膩,通曉世事。她的外表乾淨俐落,安靜沉穩,個頭嬌小,跟我差不多高,頭髮烏黑柔滑,剪了一個她所稱的「香奈兒鮑伯頭」,而且用眼線筆畫出完美的電眼。她的唇邊有道薄薄的美人鬚,但從未試圖掩飾,因為她肯定知道這樣讓她更具魅力。但她總是壓低嗓門說話,好像她跟你說的全是祕密,這或許是她自小養成的習慣,畢竟她小時候伊朗正在鬧革命,人人都需謹言慎行;這也可能是她少女時代養成的癖好,因為當年她看上眼的男孩和男人,莫不很快就超過她家人所能容忍的極限,她不得不審慎行事。通常在星期天、閒來無事之時,我們三人經常整天窩在索拉雅和瑪莉的臥室裡,一邊聽錄音帶,一邊聽索拉雅講述她的情史和她跟那些男人做過的事情,她嘴角叼支菸,聲音因為抽了菸更加低沉。如果我始終沒被她說的事情嚇到,部分原因在於我還不了解性事,更別提帶著色情的性事,致使不太明白對於性事應該抱持什麼期望。但我之所以沒被嚇到,原因也在於索拉雅冷然的語調。她講得雲淡風輕,好像什麼都打不倒她。但我猜想她覺得她必須試試自己有多少斤兩、探測自己具有多少與生俱來的實力,若是這股實力無法保護她,情況又會如何?她描述的性事似乎談不上歡愉,反倒像是某種她甘於承受的實驗。只有在這些東拉西扯的故事中,她才會提及德黑蘭,而只有在說起德黑蘭的種種過往之時,她才真正喜形於色。
◆◆
十一月,飄了雪;當那位商界人士出現在我們的談話裡,肯定已是十一月間。他是荷蘭人,年紀是索拉雅的兩倍以上,他住在一棟沒裝窗簾、位於阿姆斯特丹運河畔的房子裡,但他每隔兩星期就到日內瓦出差。我記得他是個銀行家。我也記得他家裡沒裝窗簾,因為他跟索拉雅說他操幹他太太的時候一定開著燈,確保紳士運河對岸的人們可以看著她。他下榻皇家旅館,索拉雅的叔叔有次帶她去旅館的餐廳喝下午茶,她就是在那裡頭一次遇見他。他跟她隔著幾張桌子,當她叔叔操著波斯語嘮叨抱怨他的孩子們揮霍成性,索拉雅看著銀行家優雅嫻熟地幫盤中的魚去骨。他精準地舞動刀叉,神情極致沉穩,慢條斯理地剔除整條魚骨。人們吃魚之時不免從嘴裡移除魚骨,但他不同,他自始至終沒有從口中吐出任何魚骨。他緩緩地、一絲不苟地剔除魚骨,看起來似乎一點都不餓。然後他從容不迫地吃魚,自始至終沒有被魚骨哽到,甚至從未因為被一小根沒剔乾淨的魚骨刺到喉嚨而眉頭一皺、閃過一絲不悅的怪相。像他這樣的男人可以轉化一個本質上可稱殘暴的舉動,使之看來細緻優雅。她叔叔去上洗手間時,銀行家示意付帳、付了現金、從座位上站起來、扣上他的休閒外套,但他沒有直接走出餐廳、邁向門外的旅館大廳,反而繞過索拉雅的桌旁,在桌上放下一張五百瑞士法郎的紙鈔。他用藍色原子筆把他的房間號碼寫在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的肖像上,好像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為她獻上這個寶貴的訊息。稍後當她跪在旅館的床上、被露臺灌進來的寒風凍得發僵,銀行家跟她說他總是訂一間俯瞰湖景的房間,因為日內瓦湖的大噴泉強而有力,噴出的水柱高達數百英呎,撩撥他的性慾。她躺在艾德菲爾德太太的兒子睡過的雙人床上跟我們複述此事,雙腳懸空晃來晃去,笑得停不下來。即使她覺得此事非常可笑,他們依然做出協定。從那時起,如果他想讓索拉雅知道他即將來訪,他就打電話到艾德菲爾德太太家,謊稱他是她叔叔。至於那張五百瑞士法郎的紙鈔,索拉雅自此將之收放在她床頭櫃的抽屜裡。
(……)
◆◆
結果索拉雅自行返家。自行返家——正如她自行離家,來來去去都是她自己的選擇。那天傍晚,她穿過新綠的田野,出現在寄宿家庭的門口,衣衫散亂,但毫髮無傷。她雙眼布滿血絲,眼影糊了,但相當鎮定,連看到她爸爸都沒有露出訝異的表情,只有當她爸爸聲嘶力竭、近乎啜泣地大喊她的名字,她才稍微皺了皺眉頭。他衝向她,一時之間,他似乎打算高聲叫罵或是甩她一巴掌,但她動也不動,毫不退縮,他反而把她拉向他,緊緊擁抱她,眼中充滿淚水。他操著波斯語憤憤地、急急地跟她說話,但她多半沉默以對。她累了,她用英文說,她需要睡一覺。艾德菲爾德太太問她想不想吃東西,聲調異常高亢。她搖搖頭,好像我們任何人再也給不起她需要的東西。她朝著長長的走廊轉身,走向她的臥室。走過我身邊時,她停下來,伸手摸摸我的頭髮,然後非常緩慢地繼續往前走。
隔天她爸爸把她帶回巴黎。我不記得我們是否說了再見。在我的記憶中,瑪莉和我認為她會返回寄宿家庭,我們覺得她會回來把書唸完、告訴我們一切。但她始終沒有回來。她讓我們自行判定她到底出了什麼事,而在我的腦海中,她停駐在她伸手摸摸我的頭髮的那一刻,我想著她那略帶憂傷的微笑,深信我見證了某種優雅的風範——唯有把自己逼到盡頭、遭逢難言的陰鬱或恐懼、成功地克服了它,如此才展現得出這樣的風範。六月底,我爸爸完成訓練課程,專精於創傷醫學,將我們全家搬回紐約。九月開學,我回學校上課,班上那些刻薄的女孩對我起了興趣,想要跟我交朋友。在學校的派對上,其中一個女孩繞著我轉了一圈,而我只是沉著地、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她驚嘆我變了好多,讚美我在國外添購的衣物。我見了世面,在國外繞了一圈之後重返校園,即使我什麼都沒說,她們感覺我已通曉世事。有一陣子,瑪莉寄卡帶給我,她錄下她對我說的話,跟我說她的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但她終究不再寄來卡帶,我們也失去聯絡。對我而言,瑞士的那段過往自此畫下句號。
在我心中,索拉雅也成了過去,誠如先前所言,我始終沒有再見到她。只有十九歲的那年夏天、我暫居巴黎時,我曾經試圖打聽她的下落,甚至在那時,我也只是隨便試一試,打個電話給電話簿裡兩戶姓薩沙尼的人家,然後宣告放棄。但若不是因為索拉雅,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坐上那個年輕人的摩托車,年輕人在我公寓對面的餐廳洗盤子,有天晚上,我坐上他的摩托車,跟著他回去他在巴黎近郊的公寓,我坐在他的沙發上看電影,電影播畢之後,他跟我說,跟一個我不認識的男人回家非常危險,然後沉默地載我回去我的公寓。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跟那個比我年長、住在我樓下的男人去酒吧小酌,他不停提及他經管的夜店有個職缺,但我曉得他絕不會幫我引介,稍後當我們走回我們那棟公寓,他在他那一樓的樓梯口撲向我,緊緊抱住我,試圖把我制住,不知怎麼地,我從他的懷裡掙脫,匆匆衝上樓,躲回我那安全的公寓,但直到夏末,我始終害怕在爬樓梯的時候碰到他,經常留心傾聽他的腳步聲,然後鼓起勇氣開門衝到樓下。我跟我自己說,我之所以做出這些事情,原因在於我到巴黎學法文、打定主意要跟任何願意跟我說話的人交談。但整個夏天,我始終隱隱察覺索拉雅說不定就在附近,我跟她相距不遠,我也貼近心中的某種思緒,這樣的思緒吸引了我,卻也令我心驚,就像是索拉雅。世間有種遊戲,它攸關權力與恐懼,它不願屈從人們與生俱來的脆弱與善感,它從來不僅只是一場遊戲,索拉雅玩起這種遊戲,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投入。
但我自己沒辦法太投入。我想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那年夏天之後,我再也沒有如此膽大妄為、如此輕率魯莽。我交了一個又一個男朋友,他們全都秉性良善,也都有點怕我,然後我結了婚,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遺傳到我先生淺棕色的頭髮,她若漫步於秋天的田野,你八成很容易就看丟了她。小女兒可不一樣;她在任何場合都引人注目。她自小就獨樹一格,成長發育跟周遭眾人形成對比。我知道我不該想像一個人的容貌操之於己,這樣想是不對的,甚至很危險,但我敢發誓我的小女兒似乎自行造就了她那雙綠眼和那頭黑髮,而綠眼黑髮始終吸睛,即使當她跟其他孩童站在合唱團裡,大家也只注意到她。她才十二歲,個頭依然矮小,但當她走在街上或是搭乘地鐵,男人們已經盯著她看。她不彎腰駝背、不戴上兜帽、不像她朋友們一樣戴上耳機逃避世人,她像個皇后似地挺直站立,卻也因而更讓男人們著迷。她有一股拒絕退讓的傲氣,如果只是如此,我或許不會為她感到害怕。她對自己的吸引力感到好奇,想要探知這股力量的範疇與極限,這才讓我心驚,甚至妒忌。有天我親眼見證;一個西裝筆挺的男人在地鐵車廂另一頭看著她,眼神極為熾熱,似乎灼穿了她。她毫不畏懼地回瞪,眼神之中充滿濃濃的挑戰。如果有個朋友跟她一起搭車,她說不定會慢慢朝著朋友轉身,眼睛卻依然盯著那個男人,同時說幾句話逗得朋友哈哈大笑。就在那時,索拉雅的身影再度浮現在我的眼前,自此揮之不去,甚至可說是糾纏著我。我甩除不了她的身影。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可能偶爾遇見一個人,時隔半生,這個人、這樁事才在你心中抽芽滋生,怦然而現。索拉雅——她那道薄薄的美人鬚,她那雙眼線筆畫出的電眼,當她告訴我們荷蘭銀行家的性慾受到撩撥、她那發自腹胃的低沉笑聲。他一隻手就可以把她折成兩截,但他辦不到;要麼她已經折毀,要麼她就是不會。
(本文為《成為一個男人》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成為一個男人》 To Be a Man
作者:Nicole Krauss
出版:啟明出版
日期: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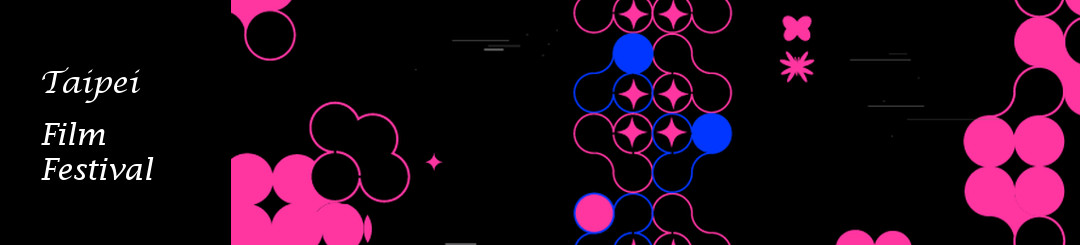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在IG上追蹤
在IG上追蹤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贊助我們
贊助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