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父過世已久,對他的記憶日漸模糊。但我還記得台灣當初剛開放「小耳朵」時,父親興沖沖的替祖父安裝,祖父第一個想看的外國節目就是固定週日中午播出的日本NHK頻道素人歌唱大賽。這個節目歷史悠久,比起現在的各種選秀來說,顯得相當單純,真的只是讓一般老百姓在電視上唱唱歌而已。
祖父是個沈默寡言的傳統男性,幾乎沒有一天不是梳著油光閃爍、一絲不苟的西裝頭。他有很多工程用的製圖鉛筆,從2H到6B都有,B的數字越高,越是柔軟容易污手。因為經常搗亂祖父的書房之故,我很小就知道,鉛筆不是只有2B跟HB而已。其實我很少跟他真正交談,因為他也很少開口說話。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祖父都是這樣,好像有一個自己的世界,相當有規律,外人無法闖入。
對於這樣的祖父來說,當明確得知他的喜好時,反而才是非常奇怪的時刻。除了他總是愛聽的美空雲雀之外,我有次終於知道他也喜歡台語歌〈雨夜花〉。那是某次家人在外頭聚餐,餐廳內有卡拉OK設備,祖父默默觀察大家唱歌很久之後,方才在兒女的慫恿下點了一首〈雨夜花〉。當時我覺得〈雨夜花〉是一首旋律很平淡的歌曲,並不了解有什麼特殊之處。而且學校告訴我們,40年代之前台灣沒有音樂可言,〈雨夜花〉是邪惡的歌曲,因為它曾經被日本人改編為招募軍伕之歌,內容又太悲哀萎靡,所以才會被政府禁唱。
「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難池。怎樣呼阮,離葉離枝,永遠無人可看見。」
這其中必然有什麼奇怪之處,如果是邪惡的事物,為什麼像是祖父這樣普通的好人會喜歡呢?只不過幼時的我,並沒有去深究這件事情罷了。長大之後,隨著時代漸漸改變,我終於知道〈雨夜花〉原為文學作家廖漢臣所作,當時名為〈春天〉,後來由音樂家鄧雨賢重新譜曲,周添旺填詞。
在祖父正值青春的30年代,周璇〈夜上海〉之類的歌曲跟他一點關連都沒有,不是他所熟知的語言,也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我跟祖父之間記憶的斷裂,很明顯的來自於學校教育。當我明確認知到這件事情時,他已不在人世。今年讀了旅法作家林莉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裡頭描述學校教育與家庭經驗矛盾到覺醒的過程,充滿既視感。
30年代之後的祖父是沉默的。他沒有學會任何新的台語歌曲,也沒有機會告訴他的子女兒孫,在戰爭末期一度入伍成為日本軍人是怎麼一回事。不管發生在他身上的是什麼事情,都只是歷史的偶然,非常偶然的生為日本人,非常偶然的效忠了這個國家,非常偶然的不再是日本人,非常偶然的又效忠了另一個國家。因為他的學習能力太好,即使我兒童時根本在父母的刻意安排之下一句台語都不會說,他也能跟我用國語勉強地溝通:「要去市場玩嗎?走吧。」作為他的長孫女,牙牙學語之際他教會我的第一首歌曲是日本演歌,但之後直到十九歲我才真的開始學習日文,去捉摸他當時的心情。當我開始學琴的第一年,隨著樂器店買來的琴譜彈奏名為〈荒城之月〉的曲調,他非常驚訝,接著跟著哼了起來。那是我少數發現他流露情緒的時刻。
「夜闌沈靜人已息,唯聞秋蟲鳴,晴空萬里無雲跡,皓月懸當空。
千古明月總相似,沈落又高升。亭亭樓閣今何在,銀輝照荒城。」
沒說出口的總是比說出口的更多。我們總是要走過長遠的路,才能發現事情表象之外的部份,才能真正在心裡重新看見當下未能看見的故事。雖然是錯過,但終究不是永遠的失去。這是我的人生之歌,它一開始曾經是我祖父的人生之歌。
原版音樂:女歌手純純演唱的〈雨夜花〉,由古倫美亞公司出品。
圖片出處:stevehm@flickr
一本書某種程度上是一副枷鎖:瓦爾澤《散步》
印卡
2013/10/23 10:00
星巴克觀察日記
朱旭
2013/10/25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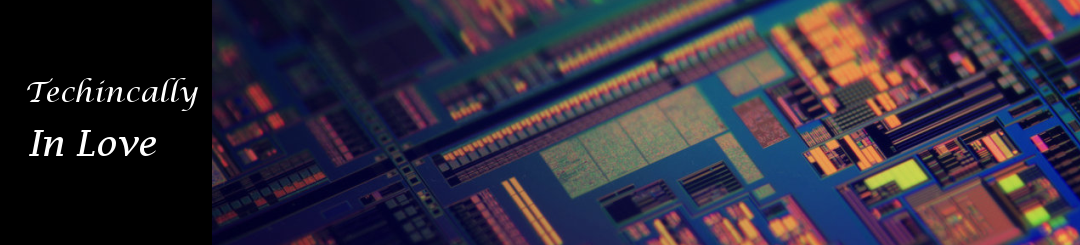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mplus
追蹤mplus RSS訂閱
RSS訂閱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
分享閱讀: